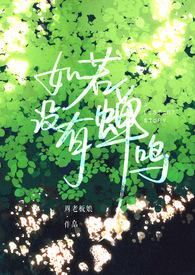大雨文学>大明:我在洪武当咸鱼 > 第24章 作死十族方孝孺(第3页)
第24章 作死十族方孝孺(第3页)
到时候有些事情可就说不清了。
于是,他干脆给自己套了个假名。
刚刚站在一旁,比方孝儒还激动的那个在胡惟庸看来最有文采的年轻士子,向胡惟庸深深一揖。
“陈兄,解缙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小弟自愧不如、甘拜下风,也感谢陈兄让我今天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名士风采!”
胡惟庸一听这名字,顿时愣住了。
解缙?
他就说嘛!
自己随便出来走走,竟然遇上个文采出众的,还以为大明的学子水平真这么高呢。
如今一看,原来是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缙!
这就完全能理解了!
整个大明二百七十年间,真正被史书记载为才子的只有三人。
第一个就是眼前这个满脸敬佩的解缙。
第二个是徐渭,字文长。
而第三个嘛,巧了,正是今天胡惟庸“写”的这首《临江仙》的原作者,杨慎!
今天可真是有意思,用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杨慎的大作,折服了另一位明朝三大才子解缙。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神奇。
和谢榛客气了两句后,胡惟庸突然问了一个问题。
“解老弟是应天人士吗?”
“不然,为什么明明带着异地口音,却在应天府参加考试?”
这一问,其实也是胡惟庸有些好奇。
因为不同于方孝孺,方孝孺是宋濂的,他出现在应天府很正常。
但胡惟庸清楚地记得,解缙应该是江西人才对。
一个江西人为何会来到应天府参加科举呢?应天府的考试难度,明显比江西高出一截。
胡惟庸心中暗想,这或许是他进一步确认此解缙是否就是彼解缙的机会。
解缙对此并未多想,毕竟这种疑问也算寻常。
谁会放着相对轻松的江西不考,偏偏跑来应天府与天下英才一较高下呢?
“实不相瞒,陈兄,小弟虽是江西人,但因家父在外为官,我便随家父一同离开了家乡。”解缙坦然答道。
“这次科考,不过是家父逼着我前来,算是一次试水罢了。”
“家父与我都没指望这次能金榜题名,只是想借此了解科考的特殊之处。”
胡惟庸听后,兴趣顿生。
原来还有这样的想法!他不禁感叹,如今的人竟如此有远见,居然懂得提前体验考场氛围。
胡惟庸毫不掩饰地竖起大拇指,赞道:“令尊此举确实高明!”
被胡惟庸这么一夸,解缙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他虽被世人称为“狂生”,实则并非狂妄,而是骨子里带着一股傲气。
但凡遇到才学、本事高于他的人,他都会心悦诚服。
解缙笑了笑,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解释道:“其实,家父的用意我明白。”
“家父认为,若我在老家参考,一旦认真考试,必定能金榜题名。”
“但我年纪尚轻,心性未定,若骤然进入官场,恐怕会因志得意满而惹出大祸。”
“所以,家父干脆让我再磨炼几年,稳一稳性子。”
胡惟庸听完,沉默片刻,随后再次竖起大拇指,心中暗叹:知子莫若父,解缙的父亲果然将他的性子摸得一清二楚。
解缙在洪武年间便早早成名,早早中举,但真正踏入官场却是在永乐年间。
然而,他在永乐朝也没能安稳几年,最终落得下狱惨死的结局。
如今看来,他不过是聪明过头、才情外溢,却对世事了解不足,自以为能掌控一切,最终翻车的神童罢了。
不过,这些事尚未发生。
眼前的解缙,不过是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还未经历那些风云变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