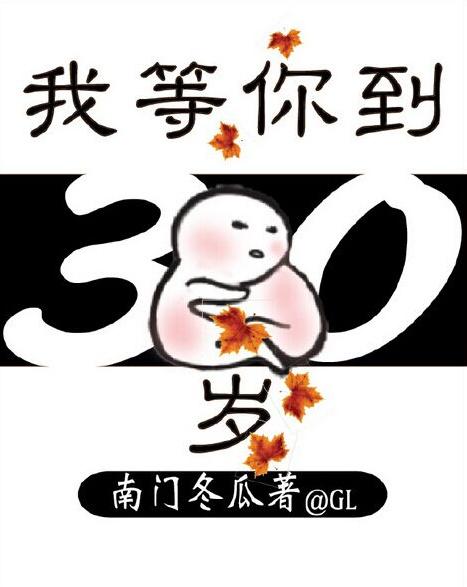大雨文学>竟不还 > 6070(第8页)
6070(第8页)
但是这棵树的枝干并没有被砍伐过,也没有被火烧的痕迹,黄大山一拍大腿:“完蛋,还真挖错坟了!”
村民评说:“黄大山啊,你居然连自家闺女儿的坟都能找错了,你这怎么当爹的。”
黄大山粗声粗气地回怼过去:“黑灯瞎火的,到处都是坟包,谁看得清楚?!”
“那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走了!”
周雅人听到此,不禁开口:“这就走?不把坟土填回去?就这么让尸骨暴尸荒野么?”
已经拎着铲子准备离开的黄大山顿住片刻,老大不高兴地盯了多事的周雅人一眼。又瞧这人的容貌气质都不凡,也不知道什么来头,于是将那点耍横的脾气压制了下去,掉头回到坟坑边:“填,当然要填,你们俩赶紧的。”而后他指使着俩小辈儿一边铲土填埋,一边不服气地小声嘀咕,“这乱葬岗暴尸荒野的还少吗。”
白冤不惯着他:“既然是你们挖错坟挖开的,让你们重新把土填回去,没毛病吧?”
黄大山梗着脖子没好气道:“我这不是在填吗,废的什么话!”
他刚说完就“啊”的一声,对面青年一铲腥土直接泼到了黄大山脸上,黄大山呸呸几口吐掉嘴里的腥土,一摸脸,火冒三丈:“干什么你,没长眼啊。”
那青年也是受到了惊吓,只觉得方才胳膊肘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又痛又麻,双手一瞬就失去控制,坟土扬了自家大伯一头一脸。
青年抱住痛麻的胳膊肘:“大伯,我不是故意的。”
而就在此刻,跟在周雅人身边的小丁瓜突然转头看向乱葬岗深处,那地方漆黑一团,仿佛被夜色罩上了一层遮盖的幕布。
他扫了眼围着坟坑的村民,大家完全没有被别的什么转移注意力,因此不太确定地问:“什么声音?”
大家正心无旁骛地围观黄大山对其侄儿发脾气,于是小丁瓜大声道:“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众人有些茫然地看向小丁瓜:“什么声音?”
周雅人问:“你听见什么了?”
没等小丁瓜回答,斜前方一阵尖叫扎破了寂夜。
村民慌了神:“咋了咋了?”
“咋回事?”
“好像是黄大嫂的声音吧?”
“听着有点像,从那边传过来的。”
众人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来此许久了,但去追铁柱他娘的黄大嫂几人居然还没回来。
黄大山一听就听出来自己媳妇儿的声音,脸色骤变,转头就往声源处冲,一边大喊媳妇儿的名字。
回应他的又是一声惊叫,村民纷纷跟在黄大山身后冲进乱葬岗,穿梭于高矮起伏的坟包间。
“快快快。”
“前面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周雅人闪避不及,被往前冲的村民撞得踉跄了几下,由于耳力受限,他只能紧紧锁定白冤的背影辨认方位,一路跟得磕磕绊绊。
小丁瓜却煞白着小脸,畏惧地盯着黑暗前方,一步步往后退,好像前头有什么无比可怕的东西。
谁都没注意到遗漏了一个小屁孩,奔在最前线的黄大山突然脚下一空,双腿失去支撑急剧坠落,发出一声惊叫。
接二连三冲上前的民众差点和黄大山一起踩空,惊心动魄地在悬崖边刹住了步子:“大山!”
黄大山惊险无比地攀住了石块,命悬一线地挂在了崖壁上,吓出来一身冷汗,再度发出惨叫。
栖息在崖下的乌鸦纷纷振翅高飞。
好死不死,黄大山那只攀住石块的手指正好被刹在悬崖前的侄儿踩住,这一脚差点儿给他手指踩扁,疼得黄大山骤然泄劲儿,就要坠崖。
千钧一发之际,一只苍白冰凉的手蓦地攥紧黄大山的腕骨,手劲忒大,将身高八尺趋于一百六十斤的庄稼汉从鬼门关一把薅了上来,跟薅葱似的扔在地上。
劫后余生的黄大山烂泥一样瘫在地上,直愣愣瞪着铜铃大眼,丢魂似的直喘气,心脏差点从腔子里蹦出来。
目睹全程的村民看看黄大山,又转向刚才将黄大山薅上来的白冤,这位大力出奇迹的英雄居然是位身板单薄的奇女子。
果真人不可貌相。
“白冤?”眼瞎耳背的周雅人紧跟而至,没弄清楚状况,就敏锐地嗅到一股血腥味,“谁受伤了?”
众人还来不及感激奇女子救人一命,也来不及安抚吓丢魂的黄大山,便看到了崖下堪称惊悚的一幕。
其实这悬崖并不算太高,约莫四五丈,若摔下去也足以丧命。
“出人命了。”白冤垂目盯着崖下,回答他,“有两人不慎坠崖,被下面的枯树枝干扎穿了身体。”
那已经遇难的二人面对着面,被一上一下地串在同一棵树干上,其中一人被尖锐的枝干扎穿胸膛,另一人则被扎穿肚腹。因为还未咽下最后一口气,四肢战栗般抽搐着。
崖下黑灯瞎火,众人只能辨认个不清不楚的轮廓,听见白冤的低语,吓丢魂的黄大山才“诈尸”般扑到崖边,仿佛认出来被树干扎穿的熟悉人影,喉咙扼住似的发出低哑的嘶鸣。
人群顿时一片哗然,纷纷找坡路下去。
待到崖下时,却又不敢靠太近。
白冤首先看清两名遇难者的面庞,正是铁柱他娘和黄大嫂,已经毫无生气地垂下四肢。两人的鲜血顺着那棵焦黑的树干流到根儿上,甘露般浇灌在土壤中。
接着响起一阵破了音的哭叫,白冤侧身让开半步,悲愤交加的黄大山擦着她衣角扑上去。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她们怎么会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