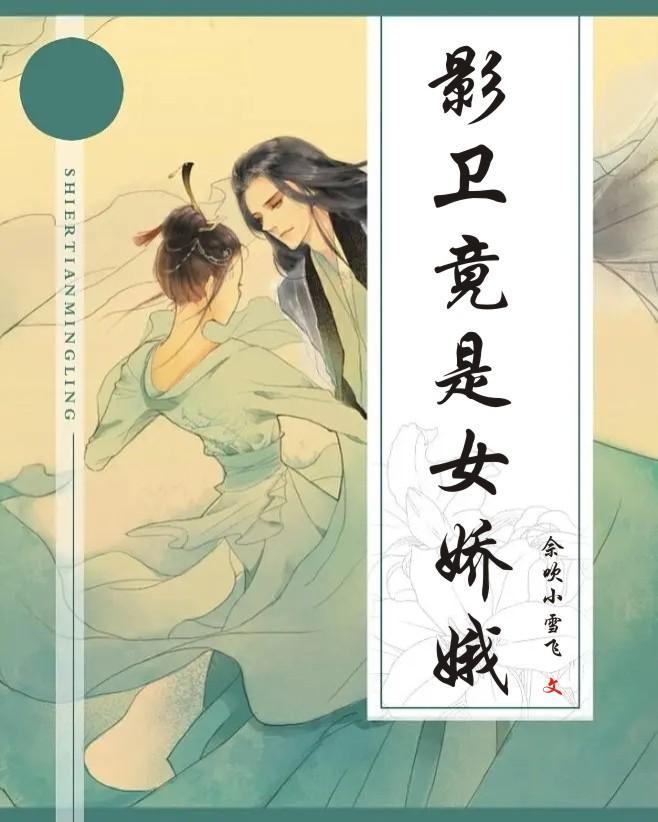大雨文学>南柯精品屋 > 卷四孤程赴微光第二十二章(第2页)
卷四孤程赴微光第二十二章(第2页)
水鬼认真地想了许久,然後摇了摇头。
“不记得了……”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海底洞xue般的沉闷和空洞,“只记得……很重要……必须拿到……”
“一点线索都没有吗?”宋乾宁不死心地追问,“写信的人是谁?收信的人呢?或者……是关于什麽事?”他试图继续去引导,“是开心的事?伤心的事?还是没见到的人,未完成的心愿?”
水鬼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店内的气氛凝重得降至冰点,只有地板上残留的小水洼在灯光下反射着微弱的光。辜曦突然开口了:“让我看看。”
他走上前去,动作利索地开始给水鬼搜身。但水和时间是这世界上最变幻莫测的东西,经过水的冲刷和时间的沉淀,对方的身上几乎什麽都没有剩下。但辜曦还是找得一丝不茍,终于,他在水鬼破旧的衣服内侧,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口袋,然後从里面掏出一件……完全分辨不出外观的东西。
辜曦把它放在桌子上。
宋乾宁凑过去看,面前的东西像是一团已经腐烂的软布,早已失去了原本的形状和质感。皮面发软发黏,边缘翘起,露出里层灰白色的断裂的纤维,如同一张发霉废弃的墙皮。内页紧紧贴合,掰开时渗出淡黄色的恶心的水痕,里面的人像和字迹早已模糊不清。
“这是一本……证件?”宋乾宁眯着眼睛看了看。
“是。”辜曦观察了一会儿後颔首,“只是不知道是什麽证。”
宋乾宁拿起那本惨不忍睹的证件,思考了两秒:“我们不知道,但有人一定会知道。”
“谁?”辜曦问。
“术业有专攻。”宋乾宁笑着说。
第二天下午,宋乾宁指挥辜曦骑着摩托,在老城区里钻来钻去,终于找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巷子深处有间破旧的铺子,门口挂着一块歪斜的招牌,上头只写了两个褪色的字:刻印。
宋乾宁下车,舒了一口气:“这家店还在,真是太好了。”
“这是什麽地方?”
“呃……”宋乾宁挠挠头,“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把学位证弄丢了,学校可以补办证明,但没有原件多少不方便,我就来这里……办了个一模一样的假证。”
“不过就用了那一次啊!”他说完又赶紧补充,“後面还是回学校开了学籍证明。”
“没想到好学生也有投机取巧的时候。”
“别取笑我啊。”宋乾宁警告,“谁还没点儿黑历史了?”
铺子里光线昏暗,碎屑飞扬,空气里混着油墨和烟丝的味道。两人一进去,一个蹲在角落里捣鼓打字机的老头就回头瞥了他们一眼。
“又来了?这回想办假学历还是假户口?”
老人的眼角布满皱纹,眼睛也深凹下去,却闪着熠熠的精明的光。辜曦一眼看出,这个人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宋乾宁嘿嘿笑了:“这回不是。大爷,我们过来,是想请您帮个忙。”
“什麽忙?”
宋乾宁从怀里拿出那团水泡软烂的东西,双手小心地托着,“麻烦您看看这东西。能看出来是什麽吗?”
老头微咪眼睛,用夹子小心地把东西夹起,放在台子上,拿放大镜仔细看了很久,眉头越皱越紧。然後,他起身拉下窗帘,拧开一盏光线白到刺目的台灯,将那件东西摊在玻璃台面下方。
灯光实在太烈,宋乾宁都忍不住闭了闭眼,老头看上去却丝毫没有被影响,依然精神矍铄,双目囧囧有神。他拿出一把已经看不出原始颜色的细刷子,小心翼翼地拂去证件表面的各种残屑,仔细斟酌辨别起来。
宋乾宁屏息等待。
“看不出内容了,但这做工我认得。”老头放下放大镜,“用这种封面材料的证件不多。”
他顿了顿,伸出手指在那一角已经模糊的封皮上来回摩挲,然後往下一揭,居然揭出一层藏在皮面底下的金属薄片——上头依稀刻着一个模糊的字母:P。
“P……新闻记者证。”老头笃定地说,“不过不是官方的那本。这种在皮壳里嵌防僞金片的做法,是十年前省台那一批记者证特有的工艺。现在早都不用了。”
“记者证?”宋乾宁轻声重复。
“准确地说,是省台专用的工作证,大概在十一二年前就停发了,我要不是偶然经手过一本,现在也不一定能认出来。”老头啧啧称奇。他说完,又擡起眼看向宋乾宁,“你从哪儿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