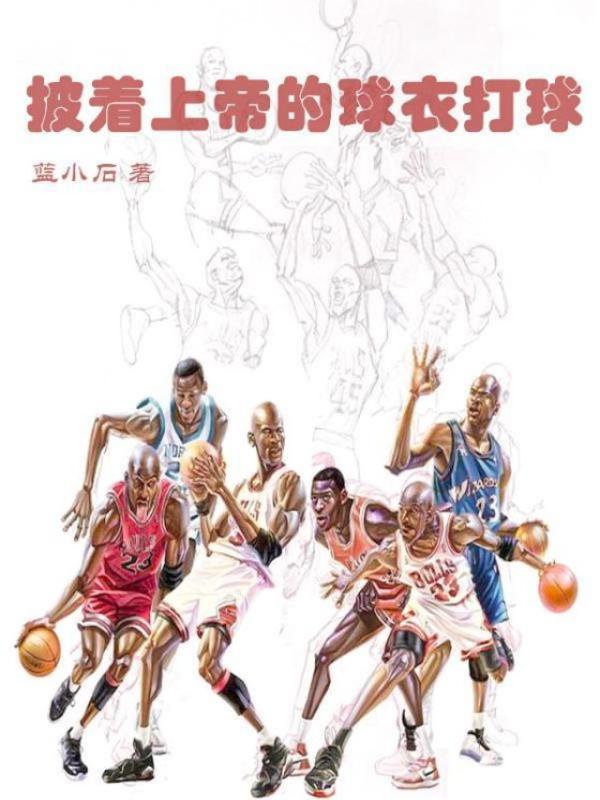大雨文学>抢七 > 第75章 重啓(第2页)
第75章 重啓(第2页)
正说着,任子延将半醉的姑娘搀出来。楚雯看过去,正是之前在洗手间打电话的人。
老杜三步并两步迎上前,欲搭手被旁边的食客拦住,立刻换作笑脸应和,“得咧。三瓶百威,马上来。”
楚雯循窗而望,一双背影正在往主路去。她收回视线,肚子开始莫名绞痛,疼得好似浑身都在打颤。从包里翻出止疼片,就水咽下。
很快任子延回座,轻描淡写解释一句,“认识。喝多了。”
楚雯暗自用拳头抵住小腹,掩饰住表情,“老杜说了。”
任子延点点头,继续未结的话题,“我刚才没有说你或者小吴工作失职,好,我承认我有点生气,但那……”
“任子延,”楚雯定定看着他,“我不是你的同事,更不是你的下属。甭用带你自己团队那套来管别人,你不觉得管得太多?”
任子延瞬间僵住,没有作声。
“我吃完了。”楚雯抄起包站起来,“没喝酒,开车来的,不用送。”
当天晚上,任子延给楚雯发去一条消息,“话说重了,别忘心里去。”他猜她在怄气,便也没期待立刻收到回复。第二天下午,任子延又发一条,“明天我送你去机场?”依旧石沉大海。
就这样过了一周,求助无门的任子延一通电话打到吴花果手机上。
吴花果正和钟世在超市排队等待结账,看到屏幕上的联系人先是疑惑地“嗯”一声,而後接起,“子延兄,怎麽想起给我打电话?”
“小吴,”任子延听得那头有杂音,问一句,“说话方便吗?”
“方便。怎麽啦?”
“那什麽,楚雯这两天跟你联系了吗?”
“昨天通过电话。你知道她出差了吧?”吴花果捂住手机话筒,对身後的钟世比个“楚雯”的口型。
钟世心领会神指指门口,示意她找安静地方接听。
吴花果点头,边走边用手按住另一只耳朵,任子延的声音这才清晰些,“知道。她去上海前我们吃了一顿饭,有点不愉快,整整一周都没回消息。我不太放心。”
“怎麽不直接打电话?”
“怕打扰她工作。本来行程就紧张,我也知道跟赛比坐办公室累。”
吴花果笑,“人好好的,那你还不放心什麽。”
“我怕她情绪不好,心里赌气总归不是好事儿。”任子延轻微停顿,“那天吃饭我们聊到她换下你去跟赛,可能我话说得重了,让楚雯觉得我在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但小吴,我完全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团队里大家各有分工,不该把个人情感带入工作。”
吴花果从任子延的表述中猜出大概,虽然楚雯完全没有提及这场不欢而散。
她回一句,“雯子的确是考虑到我才主动申请的。我……有点私人原因。”
“能理解。这几天我也反思过,哪怕有个头疼脑热换个人去出一线,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不该那麽说。”
任子延这人,经历丰富,身经百战,城府深,想得多。某种层面是坏事,总觉得他留有後手,凡事注定是不能吃亏那个;某种层面却又是好事,懂得变换立场,会深刻自省,既然不妥那就竭尽全力补救。
最初吴花果不喜这种性格,接触多了却也觉得树有千种人有万类,品质正直,能够对身边人坦荡,至于其他——安妥于世的成年人,谁逃得过“社会性”?
“以我对雯子的了解,她不会因为觉得别人挑拨就自己生闷气。”吴花果想想问道,“你们吃饭还有别的事儿吗?”
这是一种女友间不言而喻的信赖——她怎麽样,我们之间怎麽样,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犯不着为无关痛痒的评价大动肝火。
任子延听罢,原原本本将当日发生叙述一遍。末了无奈总结,“大半个月没见,总共就呆了一个小时。我也是欠得慌,非得唠什麽世锦赛。”
吴花果明晰了事情经过,心中已有答案。可她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提出一个问题,“子延兄,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为什麽会生气?”
即便认为楚雯主动提出跟赛这个行为不妥,那也应该抱着互相讨论丶给出意见的态度,其中绝不会掺杂进气恼。归根结底,任子延生气的点在于——跟赛要出去大半个月,在此之前两人已经见面寥寥,他认为楚雯没有将“他们”列入考虑范围。
钟世提两个购物袋走近,吴花果见状去接,他故意将看似体积小的袋子勾到她手上。仍在打电话的人未料到重量,手坠了一下,钟世立刻又接了回来。吴花果自知上当笑着使劲拍他,探头看过去,袋子里装了一整个浑圆的西瓜。
原来已经到吃西瓜的季节了。
“既然你生气的不是跟赛这事儿,”吴花果听着那头没反应,语音带笑补一句,“那雯子真正气的应该也不是这事儿。”
“懂了。”任子延回应道,“小吴,谢谢点拨。”
吴花果说声“客气”收起电话,歪歪头看向钟世,“不是工作话题,但非常重要。”
钟世鼓鼓嘴,“我又没问。”
走出两步,他又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过好感,很正常。”
吴花果笑了笑,挽过他的手臂。
他们之间的那座信任木桩早已深深扎进土壤里。
晚风和煦,街头熙攘,衣着鲜亮的男男女女们大声说话,城市被浪潮般的热度席卷着。好像只有夏天允许所有的肆意,又好像人们将所有的热情都留给了夏天。这让吴花果突然间想到一个词——重啓。
崭新的丶疯狂的丶不可思议的丶难以描摹的,无论什麽发生在这个夏天里,都会顺理成章吧。
正这样想着,林拓电话打了进来:
“小吴你快去看,楚雯这下真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