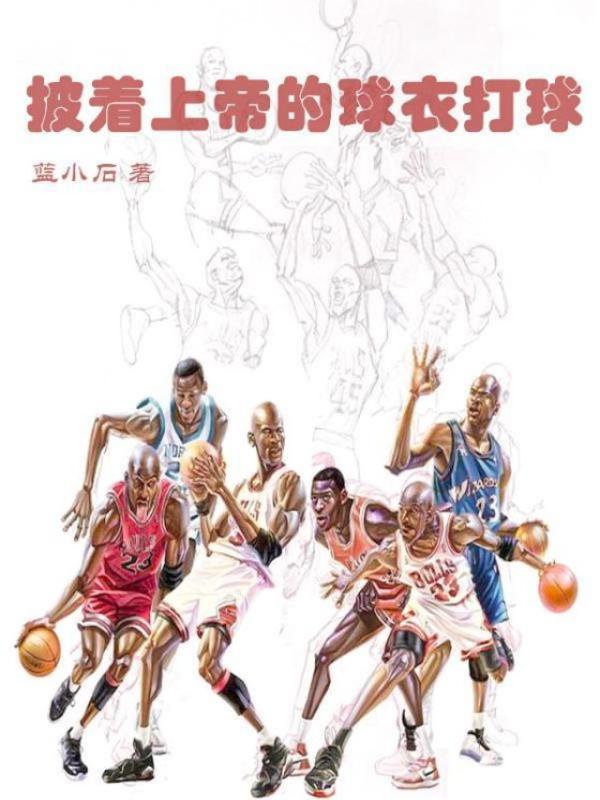大雨文学>藏君令 > 第77章(第2页)
第77章(第2页)
她心中无比清楚,死者的答案或许远远不比生者重要。
那麽帝释霄的所为,会不会和帝师有关?
而自己会不会真的做错了?
举目四望间,姜芜望着下人们惊恐的表情,短暂地想通了。
她隆起袖子,朝前迈了几步,便是此时,背後多了阵脚步声,除此之外,还夹杂着沉重的滚轮转动。
来者一老一少,老者满头白发,眉目藏锋,宽布遮掩下身,少者满脸漆黑,闷闷不乐,他们行至姜芜面前,老者强撑着身子,作势要起,他才刚用劲,少者猛地压住他的肩膀,自己跪了下来。
姜芜见状也是没辙,擡了擡手,免去他们这些礼节,果不其然,这老侯爷光是看到一个手势,笑得比谁都开怀。
曾经风光一时的侯爷,如今威风不再,好在悉心栽培的儿子秉承其愿,到了关键时候,也愿意替他在陛下面前跪上一跪。
“还不快起。”对方弯着脊背,推着轮椅往前,欣慰道,“陛下,老朽本是想大展厨艺,但是吾儿偏要添乱,这顿饭实在是吃不得了,让陛下见笑了。”
“老侯爷有心,凌煦是替您着想。”姜芜微微俯下身子,“想当初,老师常说,您厨艺了得,好酒好菜招呼,我那时便想来品尝,一直寻不得机会,今日特此拜访,理应上门备好饭菜,岂能如此亏待了您老人家。”
对方听得乐呵,神情依旧肃然,扬手就按在了凌煦的肩膀上,他谈笑道:“往事不必再提,老朽也忧心陛下徒增悲伤。。。。。。只是吾儿有逾越之处,还望陛下海涵。”
姜芜转眸看向凌煦,那张熏黑的脸还真是有些羞红了。
她移开视线,有些不恰当的话想问,碍于小侯爷在场,还真是不知道该怎麽开口。
对方这把岁数了,明显是看出了她的犹豫,没笑几下,就将自家这位闯祸精给打发走了。
姜芜见凌煦走远,推着老侯爷一路往外,停在了池边。
那池子深得不见影,偶尔冒出几条小鱼,老侯爷不等她开口,朝池里撒了几把鱼食,鱼群便疯狂聚在一处。
“陛下,老朽欠你一句。”
老侯爷拈了拈手里的残渣,长叹一声:“当年事虽过,但于老朽心里,还是道过不去的坎,陛下要如何处置,我听之任之便是。”
他屏息凝神,这位登基不多年的女帝,走到如今这个地步,已然付出太多。
在最绝望的时刻,所有人都在逼她做择,而她回宫後,只能逼着自己默默承受。
姜芜只是静了一会儿,仿佛思索什麽,便淡然开口。
“老侯爷说笑了,双股都拿来请罪了,还想拿什麽?拿小侯爷的命,换你吗?”
“陛下,这可使不得。”对方闻言,当即冷出一身汗,“老朽不敢了,只是时不时想起你老师,悔不当初。”
姜芜恍惚一瞬,看着夜色朦胧,面无表情道:“老侯爷和帝师的情谊,孤深知,因而想知道几件事。”
“第一件,帝师出山时,听说是父王三番五次去请,父王的性子,我非常清楚,要不是有利可图,也不会这般有耐性,所以里面是何猫腻。”
“第二件,帝师出征时,听说是父王力排衆议点了名,何国的宝物,我最清楚不过,但记载中,为何关于它的一切,都被人为抹去。”
“第三件,帝师自刎时,我无任何察觉,但身为好友的你,恰巧不在场,其义子却被罚了禁足也要前来,他府里的事,侯爷敢说半分不知。”
“头两件是帝怀恩,也就是帝师和父王之间的恩怨,独独後一件,是我丶帝师丶还有他之间的恩怨。”
老侯爷听罢一怔,继而也难以隐瞒。
姜芜站在他的身侧,从他口中得知,因为父王发现了西诃的存在,而那个存在是帝怀恩告诉他的。
帝怀恩想要让西诃获得南庸的庇护,却忘了西诃本就与世无争。
南庸王当然不会错失这个机会,所以表面遵守诺言,却在西诃暴露的刹那,让其成为苦难的开始。
既然是苦难,那麽只配被抹去,不配为世人所记。
等到帝怀恩反应过来时,早已无能为力,那场自刎,原来是他的解脱。
老侯爷只说了他所知的,关于府里的事,关于帝释霄,他也是一知半解。
姜芜来时备了车驾,临走时也是拜别了侯府的二位,独自回宫。
她和帝释霄的虚与委蛇,原以为是因帝怀恩的自刎而起,此刻想来,没有那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