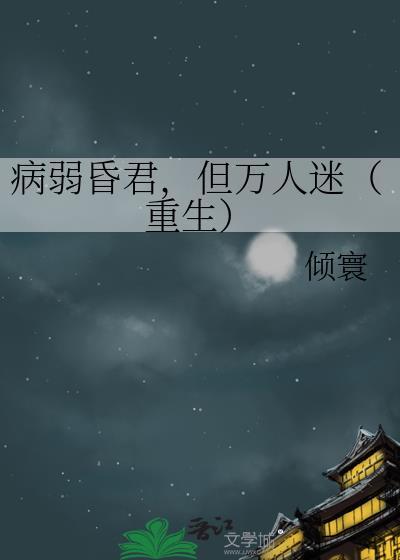大雨文学>青玉案 > 第二十章 曲流觞(第2页)
第二十章 曲流觞(第2页)
这边时珩上了马车,顾青棠正欲上另一辆马车,就见时珩拉开帘子,冲她扬了扬下巴。
顾青棠本来被一衆官员簇拥着——也难怪,时珩随形的人,忠孝仁义各个都是扑克脸,时礼礼虽然长得漂亮,可也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只有顾青棠,笑嘻嘻的,看上去很好相处。
自然,她就成了衆人打探消息的对象。
时珩这麽一叫她,她顺杆爬地就去了时珩那辆马车,这真的让她松了一口气。她最讨厌那些虚与委蛇的场面了,尤其是那些人知道她是时珩的幕僚後,溜须拍马,想从她口中探得一些消息——她看上去很傻吗?很好套话吗?
安静下来以後,顾青棠悄悄瞥了时珩一眼,他正在闭目养神。
顾青棠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刚刚低下头,就听见时珩问道:“你怎麽看?”
“啊?”顾青棠慢半拍地看向他,“哦”了一声,说道:“非蠢即坏。”
确实如此,陈乐康在这种时候摆出这样的阵仗来迎接他,让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受灾百姓作何感想?若非是有人授意,让时珩初来乍到便失尽民心,便是陈乐康太过蠢笨。
至于到底是哪种情况,如今还真是不好判断。
时珩手里的折扇在手心敲了敲,没再说话。
顾青棠还是头一次注意,他的折扇上挂着一个玉坠,用的是蓝色的锦线。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颈上挂着的玉哨,也是用的同样的锦线。
这个玉哨,在船上时,她想去还他来着。
当时时珩正在自己的房间看书,她拿着玉哨和他借给她擦泪用的锦帕去还,时珩看都没看她一眼,就说:“你自己留着吧。”
顾青棠觉得他这样的人,可能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撇了撇嘴,正要离开,时珩就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就把这条帕子送给我当回礼。”
她诧异地回身,看到时珩手里拿着她那条月白色的素布手帕,右下角,用同样颜色的丝线绣着一朵海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上面绣着精巧的海棠暗纹。
“这会不会……”顾青棠抿了抿唇,小声说:“有些太寒酸了啊?”
时珩当时是怎麽回答的来着?他举起帕子仔细看了看,手指拂过那朵暗纹海棠,笑了笑说:“我觉得挺别致的啊。”
有些莫名其妙,他拿他的玉哨和锦帕,换了她的素布帕子。
此时此刻,坐在马车里,顾青棠摸了摸自己颈上的玉哨,竟然觉得自己的双颊有些发烫。
从码头到普宁县,还有半天的车程。
期间,时珩一直在闭目养神。想起交换赠礼的事情後,顾青棠觉得有些不自在,低着头,揪着自己的衣袖,翻来覆去地折着玩儿,时间也就这麽捱过去了。
到了普宁县的时候,天色已晚。
橘色的晚霞铺满天空,将整齐的街道笼罩在其中。
这一路,陈乐康做了很好的安排,走的都是最好的路,沿路都是最好的景。这哪里像是深受水患桎梏的小镇,简直就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典范。
时珩不说什麽,顾青棠却将他的反应都看在眼里。她在心里啧啧直叹,这个陈乐康,不管是蠢还是坏,好日子都到头咯。
舟车劳顿,从马车上下来时,时珩一行人都已经累得脱形,偏偏还要强打着精神去赴宴。
用时珩的话来说就是,既然民脂民膏已经被搜刮了,那就更不能浪费了。
宴会之上,曲水流觞。
一派歌舞升平之中,陈乐康率领着衆官员不停地给时珩敬酒。时珩也不推辞,杯杯笑纳,让顾青棠十分捉摸不透。她家大人,什麽时候这麽好说话了?
当然,不解归不解,她还是该吃吃该喝喝。大人说了,不能浪费!
酒足饭饱,一曲清平乐缓缓奏起。
层层纱幔除去,一个柔软似水的女孩子被缓缓托起,立在一方白色的莲花上,她的正上方,有一方明月,将她包裹在其中,说不出的温柔可人。
这是陈曦,陈乐康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