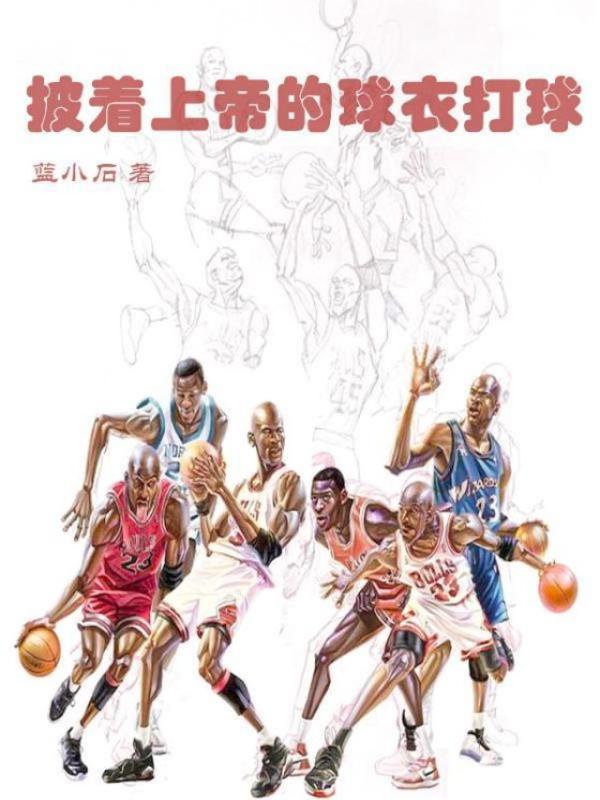大雨文学>临江辞 > 番外篇有条一针见血的评论说谢闻啰嗦看到这条评论我先是惊讶继而意识到这就是谢闻行事的特点(第3页)
番外篇有条一针见血的评论说谢闻啰嗦看到这条评论我先是惊讶继而意识到这就是谢闻行事的特点(第3页)
“也好,我会同天帝商议此事。”
一阵微风飘来,带来一缕若有若无的花香。?弹指清除死棋,剩馀棋子躺在枰上熠熠生辉。像是早就有了约定,两位神君都没有清点棋子的目数,而是笑着开始了下一局棋。
『郡主篇』烟花不堪剪
“夫人,早些休息,将军已经去了城外大营,看样子不会回来了。”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又去了军营……好容易等到他回一次京,没想到前脚见了陛下,後脚就出了皇城。自打他拜了上将,几年来踏入家门的次数屈指可数。
那些军务,当真要耗去这许多时间麽?她不晓得上将军要处理多少军务,只晓得父亲执掌三军的时候,从来不会像他这样,数年不得一日闲暇。且他自己繁忙也就罢了,还要拉着默儿一起,父子二人见天不沾一回家。
兴许真是她要得太多了吧,成婚之时,她不是不清楚他身上的重担,也做好了和他一起面对的准备。
只是做好准备是一回事,真的面对又是另一回事。空房守得多了,是个人心里都存着一股气。
何况他从不肯跟她交流营中之事,一直把她当做深宅妇人。在他眼里,她只是喜欢舞枪弄棒,全不配同他谈兵论政。
不过她也确实,很久没有碰过兵器了。掌管府中大小事务,足够她耗去大半精力,到了晚上,只想有个人在身边暖上一暖,再没有心神摆弄其他。几年下来,也不知那口青锋宝剑,有没有埋怨过她。
今夜,她突然想再看看它。
深秋的风总是很凉,即便躲在屋里,寒气也能顺着门缝窗沿渗入房间,冻得人几乎坠在冰里。受着逼人冷风,她按着记忆里的方向走了一段路,终于在尘封已久的角落里寻到那口属于她的剑,同时跃入眼帘的,还有一张粗制滥造的弓。
纤长的手指划过剑鞘,指腹所及皆为寒凉。尽管多年不见天日,鞘上的宝石也依旧光彩夺目,全不像她一样死气沉沉。
同他相遇那个午後,她佩的便是这把剑。因见春光正好,她带着几个侍女去了淮阳最大的酒楼,谁知刚坐了一刻钟,外面便有了一阵喧嚣,不少人跑出去看热闹。听他们议论,好像是父亲得胜回城,还带了不少新奇物事。
于是她推开窗子,探着头向外望了一眼。这一眼,没有看到什麽稀罕玩意,只看见一位银铠红缨的少年将军,昂首挺胸地跨坐在马上,微笑着面对百姓的欢迎。少年生得一副剑眉星目,加上满脸的意气风发,看上去竟比太阳都要耀眼许多。
更要紧的是,少年不过二八年齿,位次便已到了父亲身侧。
後来她终于晓得,那少年是江北邹家的公子邹玄,十四便进了军营,头一年崭露头角,两年下来竟已是父亲跟前的红人。
同时她也被告知,因为几代没有出过人才,邹家已经不是能和淮王府抗衡的邹家,不过现在有了邹玄,邹家复兴指日可待。
看得出来,父亲极为欣赏这位偏将,说到最末,他话锋一转,问她是不是对邹玄有意。一句话下来,她的脸便烧得火炭般烫,两只手怎麽放都不是地方。想要寻个角落躲起来,耳边又响起父亲低沉的笑。
最後她只能强撑着说,有意又怎麽的,父亲天天催孩儿成婚,难道还不许孩儿自己择夫?孩儿说过,要嫁便嫁天下第一等的少年英杰。
说的不错,只是邹玄这个英杰,性子太冷,我怕你受不住他。
不就是冷些吗?稀世大才,总归是要有点脾性的,他若跟旁人一样唯唯诺诺,孩儿还未必瞧得上他。
呵,冷暖自知的事情,我也不好多说什麽。你回去掂量半个月,倘若还想跟他一起,那我就去江北提亲。
接下来的半个月,邹玄被父亲留在了王府,而她躲在屏风後面,听他和父亲讨论军国大事。他不是沉默寡言的人,反而还颇具辩才,好几次把父亲说退三分,他行事也极有分寸,言谈看似咄咄逼人,实则处处留着馀地。
这样一位大好男儿,和性子冷清似乎关联不大,顶多是对人疏离了一点,可那是因为他们不够熟识,只要再多些时日,她定能融了他表面那层坚冰。
成婚之初,她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有了默儿之後,她发现,他当真冷到没有一丝人气。那些谈笑风生的画面,不过都是他的僞装,拆开所有逢场作戏,剩下的只有城墙一样坚硬冰冷的身心。
努力多年下来,她把自己累得疲惫不堪,可回看那人,也不过是多了只言片语。正当她决心放弃的时候,一个晴天霹雳落了下来。
林州平乱之时,他曾遇见一名美貌少女,还与对方同吃同住数日之久。
原来他从来不是真的无情,只是不肯对她动情而已。面对来历不明的女子,他可以手把手地教她做一把玩物一样的弓,还能亲自为她雕刻一枚精巧细致的吊坠。
可他的柔情都给了旁人,那她又算得了什麽?成婚多年,他对她没有半句软语,现在跑去林州跟人调风弄月,全不把她这个发妻放在眼里。
若真是她人老色衰也就罢了,可她分明也给了他最好的年华。她含苞待放的时候,他对她不屑一顾,只存了三分礼节上的恭敬,全不见半点情人间的呢喃。而今面对道旁野花,他竟下了马背停驻许久,至于倾注此生所有温柔。
面对这样啼笑皆非的结果,她一时也乱了心神,不甘之馀,她更多的是绝望。兴许真是她错了吧,不该无视父亲的劝阻。
介苍,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情意,可能不能告诉我,我是应该成全你这份难得的恋情,还是挑破真相逼你记起当日的誓言。
平乱结束,介苍率兵归来,身侧没有那位传说中的女子,腰上却多了一枚芍药吊坠。看来她无需做出选择,介苍已经有了自己的决定。
只是介苍,你既然已经放弃,为何又要留下这麽明显的念想?就算你心里想着她,可面上,是不是也该稍微考虑我一点?我才是这个家的主母,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
可他还是铲了满府的牡丹,种了一地的芍药,就像他明知道她手上有竹弓这样的证物,却还是不肯温柔半分。
一把宝剑,一张竹弓,二者差距几同云泥,却一起在暗处敛了锋芒,再没有机会重回初日模样。
时至今日,她对林州那位女子没了半点嫉恨,反而生出几分同病相怜之感。她确实得了介苍一段时日的疼惜,甚至还让介苍惦念了十多年之久。可惦念终究只能是惦念,她和介苍,到底没有终成眷属的可能。
近来默儿同一位女子有了牵扯,据说那位女子极富才干,不仅破得了李祭司的奇阵,还被朝廷派去救灾救民。
她年轻的时候,似乎也想过入朝为官,成就一番事业。只是社稷坛之外,女官毕竟只是少数,即便去了,也未必做得出什麽气候。
所以她相中了介苍,想要借他达成心愿。哪知他确实功成名就,可功名背後,并没有一分或者半分是因为她的存在。他的封侯拜将,带给她的只有空虚和寒凉,一如多年无人触碰的宝剑,拔出的瞬间甚至有了几分凝滞。
往事已矣,再没有重来的可能。她收回宝剑,听到一声嘶鸣般的长吟。灯光之下,剑柄剑鞘都褪色了几分,旁边那张竹弓也是,隐约能找到几条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