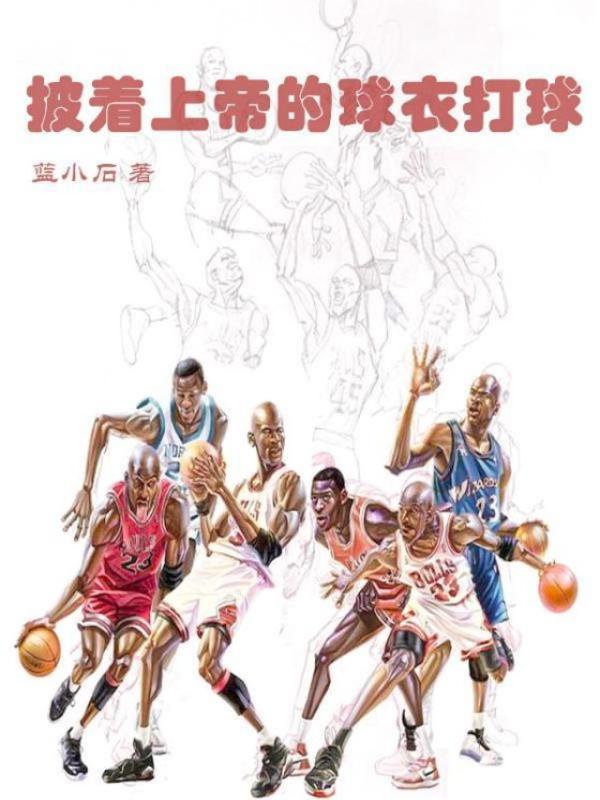大雨文学>她的罪名 > 第108章 两个只能活一个 01(第2页)
第108章 两个只能活一个 01(第2页)
严通推着自行车,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门口有一双新的运动鞋,他喊:“妈?”
黄贵兰说:“你弟弟来了,来吃饭吧。”
“哥。”小武一边动筷子,一边喊。桌上少见地有红烧肉这样的大菜,黄贵兰还在厨房忙活来忙活去,捣鼓一阵又端上来一碗青菜和一盘西红柿炒鸡蛋。
“妈,上次跟你说的事,你钱准备好了吗?”小武边吃饭边说。
黄贵兰“嗯嗯”了两声,严通问:“什麽钱啊?你又要钱做什麽?”
“哎呀,哥,没你的事,你好好念书吧。”
严通说:“是你要钱,还是爸爸要钱?”
“哥!跟我爸没关系,我这次有个好买卖,一本万利,咱家年底就能变暴发户你信不信?”
“我不信。”
“你那点见识。就是读书读傻了,有什麽用啊……”
黄贵兰说:“小武,你要跟妈说清楚,这确实不是你爸要钱吧?”
“他每天喝得醉鬼似的,哪来这心思。我是真想让咱家好啊!哥今年不就要考大学了?以後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哥,你到时候可得谢谢我,你的学费我包了。”
晚上小武和黄贵兰在房间里不知道商量什麽事,严通心烦意乱,但不敢分心,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上考场,此时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18岁时他就看清楚了一个事实,人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那麽一定要去一个新的环境,去一个能帮助自己不断向更高处前进的,一个有活力和有能动力的环境中去,人如果一直和不求上进的人待在一起,迟早自己也变得没有出息,最後就是一滩烂泥,彼此仇恨和埋怨,然後把那可悲的贫穷又通过繁衍传递下去。
那天晚上他做了两张试卷,一张数学一张英语,数学129分,英语差点91分,自己文科一直很好,能拿260以上,这样语文打个120的话,他还是有很大的希望考到长沙去。他安慰自己。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他留在教室里做试卷,又遇到了徐子扬,俩人无声地坐在座位上刷题,7点的时候,二人同时停笔,严通对了一下答案,数学136分,有点进步。他走到徐子扬座位上,问:“准备得怎麽样了?”徐子扬把手拿开,严通一瞥,发现也是数学,也是136分。
两人收拾书包回去,因为彼此顺路,两人一同走在小河边,严通问:“你想考哪所学校?学什麽?”徐子扬说:“学新闻。”
严通莫名其妙,问“新闻是做什麽的?”徐子扬说:“是让社会不要再那麽的……不公平。”
严通好奇心上来了,问:“新闻还能有这作用?”
“有。”徐子扬说:“只有时刻知道这个社会上正在发生什麽,才能明白自己正身处在什麽样的环境中,把目光从单一的人身上移开,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由看不见的「力」做牵引,一个人受苦并不全是这个人自己的问题。”
“是坏人的问题。”严通说。
“那是什麽让人变坏了呢?”徐子扬问。
严通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徐子扬说:“我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学新闻,也许能从每天发生的事情中研究出原因。”
高考的前一周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天放学严通依然留在教室做试卷,徐子扬先走一步了,严通知道他每周得有三次,去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塑料瓶,卖给废品回收站,一毛钱俩,他家里父母都不在,只有爷爷奶奶,条件不好。
回去的路上,在小河边,他看见寸头为首的几个男生在打人,把人往水里面摁,那人湿漉漉的,眼镜被打掉了,蜷缩在地上,寸头对着他的肚子又踢了一脚,严通看清楚那人是徐子扬。
他连忙把单车停在一旁,刚走两步,寸头发现了他,说:“你想帮他?你信不信,我也弄你啊?”
旁边几个人哈哈大笑,上星期这夥人放火烧了学校的垃圾站,校长把他们全部开除了。严通不知道还有什麽办法可以阻止他们,寸头说:“两个大男人天天走在一起,恶不恶心?”
徐子扬伸出手,想把眼镜捡起来戴上。
寸头又上去,勾肩搭背,说:“你现在踢他一脚,我就当你是兄弟。”
汗从额头上滴落,寸头放在严通肩膀上的手越捏越紧,三个人把他围住,寸头扣着他的肩,一人用手摁了两下他的头,一人驾着他的胳膊,後面还有个人推着他走,徐子扬蜷缩在地上,没有反抗的力气,严通看见他那双眼睛,和前几天不同,此时失去了光彩。
“人会欺负群体中最弱小的那一个,他们针对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弱小。”
在第一次一起回家时,徐子扬曾轻轻地说出这句话。
严通不想看他的眼睛,也不敢忤逆寸头,他深知如果反抗,这几个家夥什麽都有可能做得出来,徐子扬没戴眼镜,也许认不出他吧?而且他也没开口,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来了……
严通一咬牙,用脚踢了一下徐子扬的手臂,没有太用力,也没有不用力,他踢完後,寸头哈哈大笑,几个跟班也笑个不停,严通跑掉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桌前,说服自己赶紧再做一张数学试卷,但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满脑子都是徐子扬的脸,第二天去学校,徐子扬没来上学,严通问老师班长呢,老师说他不知道。
放学的时候,严通心事重重,想去徐子扬家中看看,但他并不知道徐子扬家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大概方向,他推着自行车经过小河,发现很多人围在那,他挤上去看,问大人们“发生什麽了?”
河边有一个蓝色的塑料布盖着的地方,严通没反应过来那是什麽,直到有个大爷说:“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走夜路没看清楚还是怎麽回事,掉河里淹死了。”
严通吞了口口水,问:“是谁?”
大爷摇了摇头,说:
“老徐家的那个小子,哎,造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