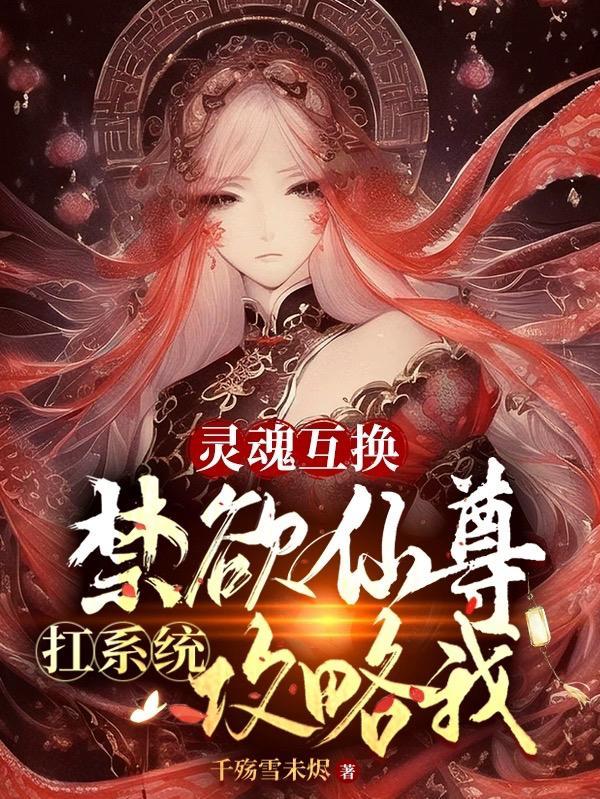大雨文学>化学博士穿越古代当军工巨鳄 > 第120章 金石为开(第1页)
第120章 金石为开(第1页)
落霞山的硝烟还凝在秋空里,带着硫磺与血腥的气息,八百里加急的马蹄声便如惊雷般踏碎了京城的平静。那封染着边关风霜的密报,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砸进紫宸殿——越王云琮,身中奇毒,命悬一线!
“哐当!”
龙泉窑青瓷茶盏在金砖地面上碎裂的声响,刺破了殿内的死寂。温热的茶水溅湿了明黄龙袍的下摆,蜿蜒如血,皇帝云霄却浑然不觉。他猛地从龙椅上弹起,素来沉稳的面容扭曲着惊怒与不敢置信,龙案上的奏章被带落一地,哗啦啦散作纷飞的蝶:“你再说一遍?越王他怎么了?!”
传信的暗卫单膝跪地,额角冷汗涔涔:“回陛下,越王殿下与赫连朔死战,中了淬毒镖箭,那毒诡异霸道,随军医官束手无策,殿下此刻已是……气息奄奄。”
“废物!一群废物!”云霄的怒吼震得殿顶梁木仿佛都在颤抖,他一脚踹翻身前的锦凳,双目赤红如燃:“传太医院所有太医!立刻!马上!去越王府!若救不回越王,朕让他们满门陪葬!”
帝王之怒,雷霆万钧。殿内宫人早已吓得匍匐在地,浑身筛糠,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消息如瘟疫般蔓延,片刻后便传到了慈宁宫。太后正捻着紫檀佛珠诵经,闻言瞬间眼前黑,佛珠“啪”地断裂,檀木珠子滚落满地,在青砖上弹跳的声响,像是敲在人心上的丧钟。“我的琮儿!”她凄厉的哭喊撕破了宫闱的宁静,若非宫人死死搀扶,早已瘫倒在地。凤眸中泪水汹涌,她抓着宫人的手,指甲几乎嵌进对方肉里:“备辇!快备辇!哀家要去看琮儿!就算是邪毒,哀家也要陪着他!”
皇帝匆匆赶来,望着母亲鬓边骤添的银丝,心中又是疼惜又是无奈。他苦劝良久,言及王府此刻混乱,邪毒恐有蔓延之险,凤体为重,才勉强将太后劝住。可慈宁宫的灯火,却一夜未熄,太后枯坐窗前,望着越王府的方向,泪水淌了满脸,将衣襟浸透一片。
太医院倾巢而出。院判陈太医带着数十位御医、吏目,提着沉甸甸的药箱,面色惶惶地涌入越王府。平日里这些悬壶济世的国手们从容不迫,此刻却个个脚步踉跄,脸上写满了凝重——能让随军医官束手无策的毒,绝非寻常之物。
临时辟出的病房内,药味与一股若有若无的阴寒气息交织。云琮静静地躺在榻上,昔日那个英姿勃、剑指四方的越王殿下,此刻面如金纸,嘴唇泛着骇人的紫黑,呼吸微弱得仿佛随时都会断绝。最触目惊心的是他肩头的伤口,周围的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墨紫色,像是被冻住的淤血,触手冰冷坚硬,竟无半分活人的温热,丝丝缕缕的黑气从伤口处蒸腾,看得人脊背凉。
“院判大人,您快看看!”内侍监尖着嗓子催促,声音里满是哭腔。
李太医颤抖着伸出手指,搭上云琮的腕脉。指尖刚一触及,他便如遭雷击,脸色瞬间惨白如纸。那脉象沉伏如石沉深潭,滞涩得如同老树盘根,一股阴寒邪戾的力量盘踞在心脉附近,像贪婪的野兽般吞噬着生机;而另一股刚猛暴烈的毒性,又在疯狂侵蚀着奇经八脉,两种毒素非但不相克,反而如胶似漆,相互滋养,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
“如何?院判大人,殿下还有救吗?”
李太医猛地缩回手,踉跄着后退两步,“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老泪纵横:“陛下!老臣无能!老臣罪该万死!”他重重叩,额头撞得金砖砰砰作响,“殿下所中之毒,闻所未闻!极阴邪气锁心脉,至刚金石毁经络,二者共生纠缠,寻常解毒之法,清热、化瘀、通络,皆如石沉大海!非但无用,反而会激化毒性,加殿下……殿下殒命啊!”
话音未落,病房内一片死寂。
以解毒闻名的刘太医不甘心,取出祖传的金针,欲以“金针渡穴”之法引导毒素。可银针刚刺入云琮的穴位,便被一股阴寒之力死死黏住,针尾迅蒙上一层黑气,如同被墨汁浸染,任凭他如何运力,都无法挪动分毫。刘太医颓然拔针,看着针尖上凝结的黑霜,面色灰败如死:“此毒……非药石能医,更兼邪祟之气,是妖法,是妖法啊!我等凡俗手段,根本无解!”
“无解……”
这两个字像重锤般砸在每个人心上。连太医院的国手们都束手无策,还冠以“邪祟”之名,这意味着,云琮真的没救了。
消息传回宫中,云霄踉跄一步,扶住龙案才勉强稳住身形。他闭上眼,深不见底的悲痛中,燃起了滔天的怒火。他猛地睁开眼,眼中只剩冰冷的杀意:“摆驾!天牢!”
天牢最底层,阴暗潮湿,水滴从石壁上滑落,滴答,滴答,像是催命的鼓点。赫连朔身披重枷,铁链锁着四肢,镣铐与石壁碰撞,出刺耳的声响。可他依旧挺直着阴鸷的脊梁,看到一身明黄的皇帝亲临,非但没有半分惧色,反而出一阵沙哑而癫狂的大笑。
那笑声在狭窄的牢房里回荡,如同夜枭啼叫,令人毛骨悚然:“哈哈哈……皇帝老儿,你终于来了!是来给你那宝贝弟弟收尸的吗?”他三角眼中闪烁着怨毒与快意的光芒,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声音阴恻恻的,“别白费心机了!这‘腐心蚀骨’之毒,是我耗费三十年心血炼制的绝毒!西域万丈玄冰下的阴铁,九幽之地百年蛊虫的精髓,再辅以七七四十九种至毒草木,阴阳相济,生生不息!”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猛地凑近,铁链拖动的声响刺耳:“莫说是你太医院那群酒囊饭袋,就是大罗金仙下凡,也休想解开!云琮会在极致的痛苦中,看着自己的经脉寸寸断裂,心脉被寒气冻结,最后化为一滩黑水!这就是你们与我‘地藏’作对的下场!哈哈哈!”
赫连朔的诅咒如同最冰冷的匕,狠狠刺入云霄的心脏。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云霄脸色铁青如铁,他死死攥着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鲜血顺着指缝滴落。他没有再废话,拂袖而去,那背影里的绝望与杀意,让随行的侍卫都不寒而栗。
回到宫中,面对太后那双布满血丝、满是祈求的眼睛,云霄只能沉重地摇了摇头。太后身子一晃,瞬间苍老了十岁,她闭上眼,泪水无声滑落,慈宁宫的死寂,比任何哀号都更令人心碎。
然而,就在这弥漫全城的绝望之中,越王府内,有一个人,始终没有放弃。
秦佳喻。
她站在病房外,听着太医们的断言,听着府中人压抑的哭声,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可那双琥珀色的眼眸里,没有丝毫慌乱,只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冷静与专注。在她药物化学博士的认知里,世间从无“无解之毒”,所谓的毒,不过是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所谓的“邪祟”,不过是未被认知的能量属性与物质结构。
她抬手拭去眼角的湿意,转身对影七吩咐:“将隔壁房间清空,所有药材、矿物、琉璃器皿、玉杵铜钵,还有我设计的水浴装置,全部搬过去。另外,取毒镖残片和殿下的毒液样本,立刻送来。”
她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影七虽心有疑虑,却还是立刻照办。
临时改造的“实验室”里,灯火通明。太医院送来的珍稀药材、王府库房珍藏的奇矿异石,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案几上,井然有序。琉璃烧杯、玉制漏斗、刻度精准的铜制戥子,还有那个由秦佳喻亲手设计、以炭火加热、水层控温的水浴装置,构成了一个越时代的制药空间。
秦佳喻先拿起那枚夺命的毒镖。镖身非铁非钢,入手沉重异常,带着刺骨的寒意,上面雕刻的扭曲纹路,像是某种邪恶的符咒。她用玉刀小心翼翼地刮下一点残留的毒液,置于洁净的琉璃片上。那毒液粘稠如膏,色如浓墨,在灯火下隐约反射出细碎的金属光泽,仿佛有生命般微微蠕动。
“质地粘稠,密度极大,含有未知重金属微粒。”她低声自语,用玉簪蘸取少许,凑近鼻尖轻嗅。一股混合着腥甜与硫磺的刺鼻气味直冲脑海,让她忍不住皱紧眉头,“气味复杂,含硫元素,强还原性,对玉石有腐蚀性……”
她将毒液滴在银簪上,银簪瞬间变黑,出轻微的“滋滋”声。又取来少许药材汁液与之混合,两种液体接触的瞬间,便剧烈冒泡,化为一团黑雾。
“不是单一毒素。”秦佳喻的目光骤然锐利起来,像是穿透了迷雾的利刃,“一股是至刚至烈的重金属毒,如同跗骨之蛆,破坏细胞机能;另一股是至阴至寒的生物毒,源自蛊虫,能停滞气血,侵蚀生机。二者在炼制时形成了稳定的复合结构,阴阳相生,互为屏障,这才是解毒的关键难点。”
破局之道,在于打破这种阴阳平衡。必须先以阳和之力融化阴寒,松动毒素的共生结构,再针对性地中和清除金石之毒。若是本末倒置,直接用猛药攻毒,只会让两种毒素相互激化,加云琮的死亡。
思路既定,秦佳喻便开始了一场与死神赛跑的配伍实验。她在数百种药材中筛选,最终选定了几味药性温和、能通络护脉的药材作为基底——云琮的经脉已千疮百孔,绝不能再承受半点刺激。
随后,她的目光落在了案几角落的一块奇石上。那是“赤炎石”,产于西域火山腹地,通体暗红,触手却带着奇异的温润感。据典籍记载,此物内蕴精纯阳和之气,是驱散阴寒的圣品。可赤炎石性烈,直接使用无异于饮鸩止渴,会瞬间灼伤云琮本就脆弱的经脉。
秦佳喻凝神思索,指尖划过一堆药材,最终停在了一颗形如琥珀、质地晶莹的“血晶菩提”上。这是她偶然所得的奇药,性极平和,却能如海绵般吸收并缓慢释放其他药物的药性精髓,是调和猛药、引导药力直达病灶的绝佳载体。
“就是它了。”
炼制过程,比绣花还要精细百倍。秦佳喻将赤炎石置于玉钵,加入甘草、麦冬等缓和药性的辅药,手持玉杵,沿着特定方向,以均匀的力道反复研磨。成千上万次的研磨,让她的手臂酸痛难忍,额角的汗珠顺着苍白的脸颊滑落,滴落在玉钵中,与药粉融为一体。她却无暇擦拭,眼中只有那逐渐变得细腻如尘的药粉。
研磨完毕,她将药粉倒入水浴装置的琉璃瓶中,精确控制水温,进行长达三个时辰的“活化”处理。炭火的温度必须恰到好处,高一分则药性暴戾,低一分则无法激赤炎石的阳和精髓。她守在装置旁,寸步不离,时不时调整炭火,目光专注得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这瓶药粉。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