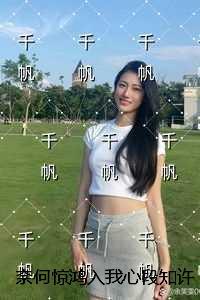大雨文学>和脱衣舞女郎妈妈一起穿越到异世界 > 第16章 妈妈的脱衣舞表演(第6页)
第16章 妈妈的脱衣舞表演(第6页)
停在那丁字裤边缘露出来的一点点白肉上。
他张着嘴。
那嘴张着,合不上。口水从嘴角淌下来,淌过那圆圆的腮帮子,滴在那绸子的便服上。
我站在角落里。
站在那昏黄的暗影里。
戴着那黑面具。
望着这一切。
那副使已经退出去了。门关上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那胖子,母亲,还有我,那个戴着面具的“乐师”。
母亲动了。
她转过身。
那动作很慢。
很慢。
她转过身的时候,那臀在我眼前一晃——那浑圆的、挺翘的、被黑丝裹着的臀。那两瓣臀肉在那光里一晃,一晃,像两团会动的云。
她面对着我。
面对着我这个角落。
面对着我这个戴着面具的人。
她看见我了。
那眼睛亮了一下。
就一下。
可那一下里,有东西——是意外?是惊喜?还是那种“你怎么来了”的光?
可那光只是一闪。
一闪就没了。
然后她笑了。
那笑从那嘴角溢出来,从那粉粉的新肉旁边溢出来。
那笑不是对着胖子的。
是对着我的。
是对着那个站在角落里、戴着黑面具、假扮成乐师的人。
那笑里有话。
那话是——看妈表演。
她转回头。
又面对着那胖子。
那胖子还在望着她。
那眼睛还黏在她身上,黏得紧紧的,黏得像要把她整个人都吞进去。
她开口。
那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春风。
“公孙大人——”
那四个字从那嘴里出来,甜得像糖。
那胖子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那笑从那圆脸上溢出来,堆在那两片厚嘴唇旁边,堆得那脸都变形了。
“夫人——”他说,那声音从他那个圆圆的肚子里出来,闷闷的,沉沉的,“夫人请坐。请坐。”
母亲没坐。
只是站在那儿。
站在那榻前面。
站在那光里。
那胖子搓了搓手。
那手胖胖的,白白的,像两个刚出笼的馒头。他搓着,搓着,搓得那手心都红了。
“夫人——”他说,“本官——本官久闻夫人乃天人之姿。昨日一见,果然——果然——”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奈何惊鸿入我心段知许江疏桐:全文+结局+番外段知许江疏桐
- 段知许心头一震,猛地转过头去。那一瞬间,他几乎以为那是江疏桐。可当他看清来人时,才发现是段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