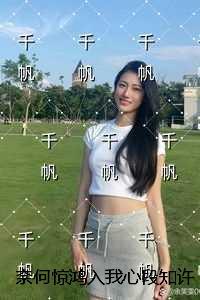大雨文学>综影视:帮助女配逆天改命 > 陈情令阿苑番外3(第3页)
陈情令阿苑番外3(第3页)
他从来没有来过。
直到我写信给他。
“景仪,”我写,“莲花坞莲蓬熟了,你来不来?”
他第三天就到了。
御剑来的,落地时气息还有些不稳,额角挂着汗。
他瞪着我,想说什么,大概是埋怨我这么突然邀他、害他连夜赶路云云。
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走过来,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
“聂苑,”他说,“你是不是长高了?”
我笑了笑。
“景仪,”我说,“你是不是还是这么多话?”
他愣了一下,然后恼羞成怒地锤了我一拳。
我也锤了回去。
我们站在莲花坞门口,像小时候在云深不知处后山那样,你一拳我一脚地闹起来。
江祖母从廊下经过,看了我们一眼,摇摇头,笑着走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些朋友,无论多久不见,都还是从前的模样。
蓝景仪的到来,果然让金凌无暇再盯着我了。
他真的太能说了。
从早到晚,从屋里到屋外,从剑法到典籍到世家名录到蓝氏家规第两百三十七条——他什么都能拿来跟金凌辩论。
金凌起初还板着脸跟他理论,后来渐渐招架不住,开始躲着他走。
可蓝景仪是那种越躲越来劲的人。
“金公子昨日那套剑法,起势时重心偏左三寸,你若不信,我们可以当场比划——”
“金公子说蓝氏家规过于严苛,不知你读过几条?读过几条便敢妄加评议——”
“金公子——”
金凌面无表情地从我身边走过,拳头攥得死紧。
我低头喝茶,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如梦坐在我对面,捧着一碗莲子羹,看看金凌远去的背影,又看看我,忽然笑了一下。
“阿苑哥哥,”她说,“你是故意的。”
我放下茶盏,认真地看着她。
“是。”我说,“我故意的。”
如梦眨了眨眼,没有生气。
她只是舀了一勺莲子羹,递到我嘴边。
“那景仪哥哥会生气吗?”她问。
我张口吞下那勺甜羹。
“不会。”我说,“他就是来帮忙的。”
如梦点点头,没有再问。
阳光从窗棂漏进来,落在她乌黑的顶,落在那碗还冒着热气的莲子羹上。
她低头小口小口地喝着,睫毛在眼底投下两小片温柔的阴影。
我看着她。
想起很多年前,她还在襁褓里,小小的手握着我的一根手指,怎么也不肯松开。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奈何惊鸿入我心段知许江疏桐:全文+结局+番外段知许江疏桐
- 段知许心头一震,猛地转过头去。那一瞬间,他几乎以为那是江疏桐。可当他看清来人时,才发现是段之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