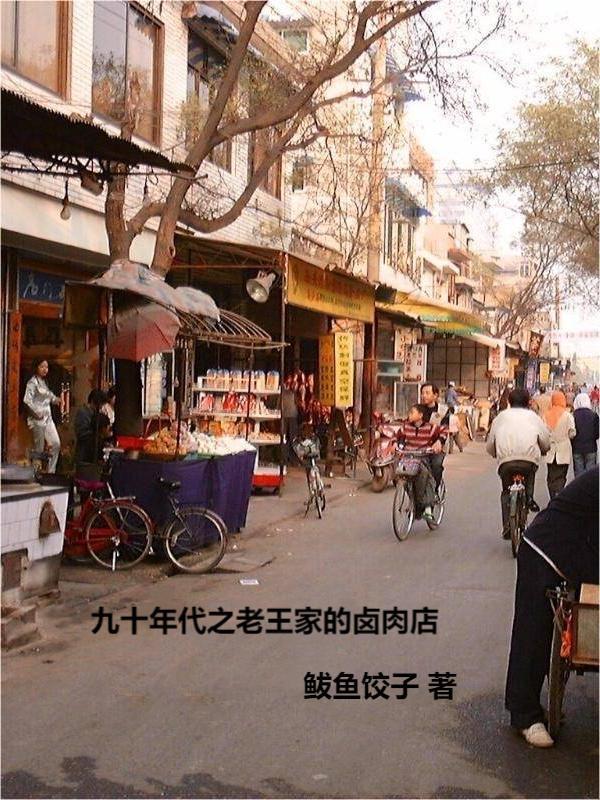大雨文学>港片:脱离洪兴之后彻底崛起 > 第572章 又一个春天(第3页)
第572章 又一个春天(第3页)
---
高晋那年春天收到第七本书。
还是寄自陌生地址,还是那期《科学与社会》。扉页上还是那行字,笔迹一样,用力,墨洇开了:
“有人传了。”
七个字。
和前六本不一样。前六本都是四个字,这一本是三个字。
但他知道,是同一个人。
他把这本书和前六本放在一起。七本一模一样的旧期刊,七行字,同一个笔迹。
他坐了很久,看着这七本书。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把它们一本一本拿下来,在桌上排开。
“有人问了。就够了。”
“有人传了。”
“有人接住了。”
“有人知道。”
“有人记得。”
“有人还在。”
“有人传了。”
第一本和第七本,都是“有人传了”。
他看着这两行一样的字,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坐下来,开始写。
写给那个不知道是谁的人。
他在信里写:您传了七年。我收了七年。现在,该我传了。
他写完了,装进信封,贴上邮票。
还是那个地址。假的,不存在的。
但他寄出去了。
他知道寄不到。
但他知道,有人会收到。
---
那年春天快过完的时候,铺子里出了件事。
那个不爱说话的男孩走了。没打招呼,没留话。早上没来,中午没来,晚上也没来。
女孩等了三天。给他打电话,关机。去他租的房子找,房东说已经退租了。
她一个人坐在案板前,坐了很久。
男孩子——现在是老师傅了——走过来,在旁边坐下。
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女孩说:师傅,我是不是教得不好?
男孩子说:不是。
女孩说:那他为什么走?
男孩子想了想,说:他有自己的路。
女孩说:可是他还想出师呢。
男孩子说:出师不是拿到什么证书。是他知道自己想不想要这门手艺。
女孩说:那他不想要吗?
男孩子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