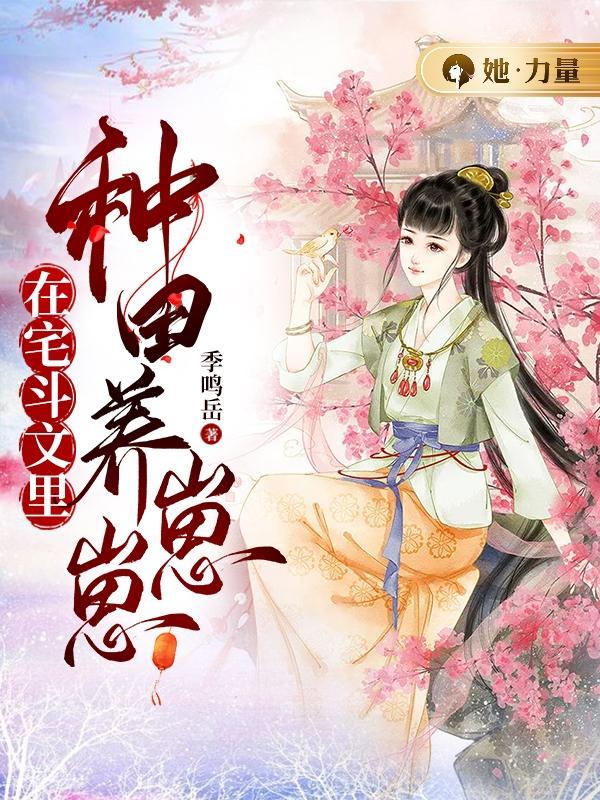大雨文学>首席交易官 > 第121章(第1页)
第121章(第1页)
她低声问周朗:“你说……你会不会有时候也觉得,是我逼死了他。”她也知道词不达意,又补充道:“我是说,如果我不找他画最后那件画——”
“那他就还挣扎在一件画五千块的泥淖里,爬不上来。不知道出路在哪里,逐渐失去创作的信心,越来越萎靡。直到有一天,罗言珠也看不上他,不再需要他,彻底断掉他的经济来源……”
“这些我都知道。”言夏说,“我没法说服自己的是他最后出现在监控视频里,那个精神恍惚的样子……”不是车冲他过来,而是他冲车过去;交警判定车主没有责任,送医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
“他沉浸其中。”周朗领会到她的意思。
“嗯。”
周朗知道安慰不到她。他想了想:“我教你击鼓好不好?”
“好。”
言夏也不知道周朗为什么会选择击鼓,还不是西方更常见的架子鼓——“就《爆裂鼓手》里的那种……”言夏记得那个电影,血从男主角的额角流下来,模糊他的视线,狂热的视线里全是鼓。
周朗的回答很无赖:“大多数时候人碰上命中注定,就会有那个意识,“就是它了”——像你碰上我。”
言夏:……
周朗把鼓槌交给她:“试试轻重。”
“敲击鼓心——听听这个声音。”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言夏似泄愤一般,一口气连击百十下,所有的力气都投掷进去,到停手,筋疲力尽,汗湿重衣。
周朗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击鼓。”
8
网上的风暴总是骤然而起,你猜不到明天的热点是什么,但是痛点总是那些。眼前茍且,远方与诗,朝九晚五之前的热血与梦想;小镇做题家想过的明天;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生老病死。
艺术那么遥远,但是石生泉像是触手可及的一个人。他会在晚上九点半之后去超市和小菜场,因为能打五折,“但是叶子菜就真的不新鲜了”;听说有羊毛可薅也会兴致勃勃试着操作,但是多半无功而返,“秒杀什么的就不是为我辈而设”;他不吃盒饭,“盒饭太贵了”,但是水果必不可少。
“打折的水果还是很便宜的,19块9的车厘子谁吃谁知道。”
“购物车里放了49999的货,最后看着两块五毛五的优惠券百感交集。”
人们很快找到他的社交账号,七百多个粉,不算活跃,也没有开半年可见;早几年会放图,有人说他画得不好,他也不反驳,但是默默把人拉黑了。
他的同学回忆:“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有点胖的男孩子”、“不怎么爱说话”、“反应有点慢,总心不在焉的样子”。
没有“学霸”、“学神”之类的光环,也没有特别的特立独行——似乎就是个混吃等死的死胖子。
唯一的例外可能几乎所有人都感叹了一声:“没想到他还在画。”
也有画廊老板绞尽脑汁想要蹭上热点,但是太难了:这位画者似乎从未参加过饭局,也没有在什么时候进入过他们的视野;他无声无息地画着,然后无声无息地死了。如果不是在死之前交出了这件作品,拍卖出天价,也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样一个人曾经存在。
到终于有人发现亮点:“资本家太黑了吧,五千块——现在得卖出多少钱啊!搞不好就是资本家在炒作!”
有艺术专业人士反驳:“不能这么说,《挽歌》确实好,虽然看不到原作,看图录就知道是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其他作品再怎么样。应该都在那位言小姐手里,她说下下周拍卖,到时候就能看到了。”
“有没有点阅读能力啊!”有人说,“那位言小姐说得清清楚楚,之前作品都不在他手里,她手里就只有《挽歌》,已经卖掉了;拍卖的是他死后言小姐一次性收购的,以半成品为主,成品就七件。”
“那之前的作品呢?”
“说是订制,就五千块一件,言小姐从他的社交软件里找到的消息。”
“五千一件,扣掉颜料和画布,这是艺术界的打工人啊!”
“比打工人还惨好吗!”
又有人跳出来说:“那也很黑心啊,就光那件……什么歌,60万订制,卖了1400万……美元!换算一下,九千万人民币,上银行打劫都没这效率!”
“这个言小姐是言夏吗?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眼熟呢,想起来了!她上次是不是……她姐姐还是妹妹坑了人家两个亿是不是?”
“好黑!”
“好家伙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是!她定制的,换句话说,在成品出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能拿到个什么东西。这特么是开赌石啊!要你出60万你干不干?你看看之前……不知道什么人,定制就五千,言小姐够厚道了。”
“但是人家死了啊。给人家父母多一点不好吗?”
“你给啊!慨他人之慷倒是起劲,人言小姐的钱就是大风刮来的?”
又有自称业内的人说:“说穿了那件东西不落在她手里,就根本不值钱。国内油画市场就这么大,拿到也不一定有人肯买。言夏是沾了周朗的光。周朗你知道伐,没他的面子,高古轩肯收?国内画廊都不肯收好吗!”
言夏没有细看网上的评论,只要没有一边倒攻击她吃人血馒头,就不必额外处理。何况她一早就准备了专业人士随时解答。
她等的是电话。
最早接到是孙楚蓝的电话,她不与她客气,开口说的是:“你没有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