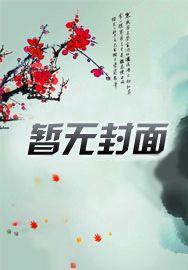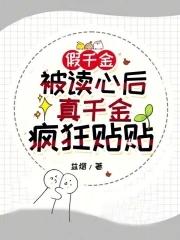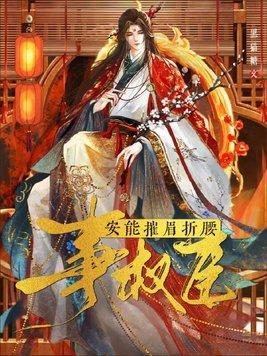大雨文学>阿耶玳,苗语,我们的根 > 第74章 危机化解(第2页)
第74章 危机化解(第2页)
老墨师开始哼唱一首奇怪的歌谣,节奏时快时慢,像是模拟心跳。龙安心跟着节奏下锤,铜钉随着歌声一点点深入。奇妙的是,每钉一下,鼓楼的吱呀声就减轻一分,仿佛这歌声本身就是一种修复力量。
"这是《营造歌》,"钉完第三根钉子后,蒙阿公解释道,"每个榫卯都有自己的节奏,顺着它,木头就听话。"
龙安心看着老墨师布满老茧的手指在木构件上游走,像医生诊脉一样精准地找到每一个应力点。那些看似随意的敲击和按压,实则都有深意——这里需要加一片楔子,那里要削去一点多余。。。没有图纸,没有测量工具,一切知识都储存在那双见证了近一个世纪风霜的手中。
"阿公,"龙安心忍不住问,"您是怎么学会这些的?"
老墨师正在调整一个隐蔽的榫卯,头也不抬:"跟你父亲一样,从唱《营造歌》开始。"他突然停下动作,指着榫卯内侧,"看这里,认识吗?"
龙安心凑近看去,在木料内侧刻着一个极小的符号——汉字"法"的变体,与苗族纹样融合在一起。
"这是。。。"
"《营造法式》的标记,"蒙阿公的声音带着骄傲,"你曾祖父龙远山从汉族师傅那里学来,又加入了苗族'鱼骨式'。"他沿着构件指示,"看这些线条走向,像不像鱼刺?"
确实,整个榫卯系统的结构酷似鱼骨——中央一条主"脊椎",向两侧分出逐渐变短的"肋骨",既保证了强度,又留有伸缩余地以适应热胀冷缩。龙安心曾在父亲的笔记中见过草图,但亲眼所见更加震撼。
"苗汉本是一家,"老墨师继续工作,声音混在风雪中,"你们汉人有文字,好记;我们苗人有歌谣,好传。各有所长,合则两利。"
龙安心胸口涌起一股热流。从小到大,他听惯了"苗汉有别"的论调,在学校因为混血身份受欺负,在广州打工时又被当作"少数民族"另眼相看。而此刻,九十多岁的老墨师却告诉他,这两种血脉在他体内不是分裂,而是融合。
"最后一根钉子,"蒙阿公递给他一枚特别粗的铜钉,"你来。"
龙安心接过钉子,发现钉头上刻的不再是苗文,而是一个小小的汉字"龙"——正是他家族姓氏。
"这是。。。"
"你曾祖父的私藏,"老墨师眼中闪着光,"专门留给重大修复用的。"
龙安心喉头发紧。这枚小小的铜钉,跨越百年时光,最终来到了他的手中。他庄重地将钉子对准标记处,举起铜锤。
"等等,"蒙阿公按住他的手,"先唱《定楼歌》,我一句,你一句。"
老墨师开始吟唱,歌词是古老的苗语,龙安心听不懂全部,但跟着音节模仿。歌声在风雪中显得格外清越,每一个音符都像有实质般撞击在鼓楼的木结构上,引起细微的共振。
"现在,钉!"
龙安心用力砸下铜锤。钉子入木的瞬间,整个鼓楼发出一声低沉的嗡鸣,像是巨兽从长眠中苏醒的叹息。紧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倾斜的东北角主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回正,所有吱呀声戛然而止,仿佛时间在这一刻凝固。
"成啦!"蒙阿公拍腿大笑,"龙家的手艺,一百年也没丢!"
龙安心呆立在原地,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他刚才参与了一场近乎神奇的修复——没有现代工程设备,没有结构力学计算,仅靠几枚铜钉、一些膏药和一首古歌,就让一座倾斜的建筑重归正直。
"别发愣,"老墨师捅了捅他,"还有最后一步——把'魂心牌'放回去,正面朝上。"
龙安心小心翼翼地取出银牌,在蒙阿公的指导下,将它重新放入顶梁的暗格中。这一次,他特意确认了方向——蝴蝶纹样朝上,汉字在下。
"这才是正道,"蒙阿公满意地点头,"苗在上,汉在下,但血脉相通。"
风雪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东方泛起鱼肚白,第一缕晨光穿过云层,照在修复一新的鼓楼上。龙安心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冻得发紫,伤腿也因长时间站立而疼痛不已,但心中却充满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下梯子时,他的体力几乎耗尽,最后几级是吴晓梅和蒙阿公架着他下来的。回到仓房,吴晓梅立刻端来热腾腾的药酒,帮他搓揉冻僵的手指。
"你做到了,"她的声音里满是钦佩,"蒙阿公从不让外人参与核心修复。"
龙安心啜饮着药酒,热流从喉咙扩散到全身:"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三个。"他看向正在火塘边烤手的老墨师,"阿公,您为什么选择教我?"
蒙阿公往火塘里添了根柴,火光映在他皱纹纵横的脸上:"因为你父亲,也因为你。"他伸出枯枝般的手指,点了点龙安心的胸口,"你有'双族慧眼',能看懂两族的秘密。"
"什么秘密?"
"远的不说,"老墨师从腰间解下那根奇特的拐杖——现在龙安心知道那是墨师专用的量尺,"就说这鼓楼吧。外人只看到外形,内行人能看到结构,但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出其中的'血脉'。"
他展开量尺,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各种刻度,有些明显是汉族的寸、分,有些则是苗族的"指"、"拃"等传统计量单位。
"你曾祖父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学会了汉族营造法,而是创造了两种度量衡的转换方法。"蒙阿公指着尺上一处特殊标记,"看这里,一寸等于多少?"
龙安心仔细辨认:"一又三分之二指?"
"对喽!"老墨师高兴地拍腿,"这就是'血脉'——让两种文化在同一座建筑里和谐共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