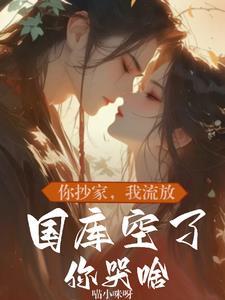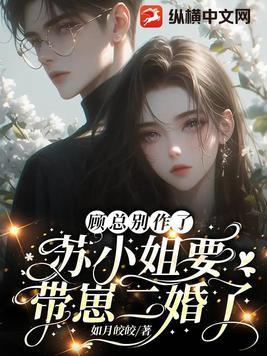大雨文学>李世民与渔家女曹婉儿的邂逅情缘 > 第174章 寒锋照胆(第3页)
第174章 寒锋照胆(第3页)
长安,太极宫,甘露殿侧的书房。
沉重的紫檀木门被猛地推开,带进一股北地深秋的肃杀凉风。
承烨一身风尘,甲胄未解,带着战场上特有的铁血与霜寒之气,大步踏入。他的目光第一时间便锁定了御案后那道明黄色的身影——大唐天子,他的父皇,李世民。
李世民正俯身看着巨大的北境舆图,眉头紧锁成一个深刻的“川”字,手指重重地敲在朔州的位置。
听到声响,他霍然抬头。父子目光在空中交汇。李世民眼中没有惊诧,只有深深的凝重、压抑的怒火,以及一丝看到儿子归来的、属于父亲的复杂慰藉。
“父皇!”承烨单膝跪地,声音带着长途奔波的沙哑,却异常坚定,“北境急报,儿臣已知!突厥颉利,背信弃义,悍然兴兵,屠戮我边民!儿臣请命,即刻奔赴朔州前线!”
李世民没有立刻说话,他绕过御案,一步步走到承烨面前。
沉重的脚步声在寂静的书房里回响。他停下,目光如同实质的探针,上上下下地审视着眼前的儿子。
承烨身上那股尚未完全散去的、源自沉霜涧的冰冷锐气,以及刚刚经历木寸冈事件后沉淀下的沉稳与决断,都让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激赏。
“好!这才像朕的儿子!像大唐的皇子!”李世民猛地一拍承烨的肩膀,力道沉雄,带着一种沙场点兵的豪迈与不容置疑的期许。
他转身,从御案旁的兵器架上,取下一柄通体暗沉、唯有刃口隐现一线青芒的古朴长剑。
剑身靠近护手处,铭刻着两个古篆小字:破虏。
“此剑名为‘破虏’,随朕征战多年,饮过无数犯境胡虏之血!”
李世民将剑郑重地双手捧到承烨面前,眼神锐利如鹰隼,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今日,朕将它赐予你!吾儿承烨!到了战场,给朕记住!你身后是大唐的万里河山,是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你的剑锋所指,当为大唐之尊严!当为百姓之安宁!奋勇杀敌,斩将夺旗!宁可血染沙场马革裹尸,也绝不可给大唐丢半分脸面!听见没有?!”
“儿臣谨记父皇教诲!剑锋所指,誓卫大唐!血染征袍,在所不惜!”承烨双手接过沉甸甸的“破虏”剑,冰冷的剑鞘入手,却仿佛点燃了胸中早已沸腾的热血。
他昂挺胸,声音铿锵如金铁交鸣,眼中燃烧着无畏的战意。
“烨儿!”一声带着哭腔的呼唤从屏风后传来。
曹婉儿在宫女的搀扶下快步走出。
她显然是匆匆赶来,髻甚至有些微散乱,脸色苍白,眼中噙满了泪水,却强忍着不让它们落下。
她手里紧紧抱着一件折叠整齐、针脚细密厚实的玄色战袍。
“阿娘!”承烨心头一酸,连忙上前。
曹婉儿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臂,力道之大,指甲几乎要嵌进他的臂甲里。
她仰着头,仔仔细细地看着承烨的脸,仿佛要将他的模样刻进心底。
泪水终究还是滚落下来,滴在承烨冰冷的臂甲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我的儿…我的烨儿啊…”
她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充满了无尽的担忧与不舍,“战场凶险…刀枪无眼…你要…你要千万小心!一定要…活着回来见阿娘!”
她将怀中的战袍用力塞到承烨怀里,“天寒了…娘给你缝的袍子…穿着…暖和…”
她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汹涌的情绪,眼神陡然变得无比郑重,甚至带上了一丝属于皇后的威严与决绝,一字一句,清晰无比地叮嘱道:
“烨儿,你记住!上了战场,对于那些丧尽天良、屠戮我百姓的突厥恶徒,杀无赦!绝不可有半分仁慈!此乃国仇家恨,血债必须血偿!”
她的语气斩钉截铁,充满了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然而紧接着,她的声音又缓和下来,带着一种悲悯众生的母性光辉:
“但是!对于那些并非本愿、被强掳驱赶上战场的可怜人,对于那些受伤被俘、放下兵刃的突厥士兵…我的儿,你要心存仁念!要好生救治,宽大为怀!他们也是爹娘生养,或许家中也有妻儿老小日夜悬望!武德,不仅在勇,更在仁!切记!切记啊!”
对恶人杀无赦!宽待俘虏!
母亲的殷切目光如同最温暖也最沉重的烙印,深深地印在承烨的心头。
这两句看似截然相反、却又在更高层面达成统一的教诲,在少年心中激荡起汹涌的波涛。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他仿佛看到战场上交织的血火与哀嚎,看到狰狞的敌人与无助的俘虏…这比沉霜涧的冰寒,比木寸冈的丑恶,更加复杂,也更加沉重!
承烨后退一步,双手抱拳,对着母亲,对着父皇,深深一揖到底。
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沙哑,却蕴含着磐石般的坚定:
“父皇,阿娘,放心!孩儿…记下了!沙场之上,儿臣手中剑,当为护国卫民之锋!心中尺,当量善恶怜悯之界!定不负父皇所赐‘破虏’之志,不负阿娘谆谆教诲之恩!”
……
朔州城头,狼烟如柱,笔直地刺向铅灰色的、低垂压抑的天空。
浓烈的血腥味混杂着焦糊和硝石燃烧的刺鼻气息,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守城将士的胸口,几乎令人窒息。
承烨一身小玄甲,外罩母亲亲手缝制的玄色战袍,手按“破虏”剑柄,挺立如标枪般钉在朔州残破的北门箭楼之上。
冰冷的朔风卷着雪沫,狠狠抽打在他年轻的脸上,却无法撼动他分毫。
他的目光如同淬了寒冰的刀锋,越过布满深深箭痕和焦黑血迹的垛口,死死钉在城下那片黑压压、如同潮水般涌动的突厥军阵上。
就在半个时辰前,突厥人刚刚动了一次凶悍的试探性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