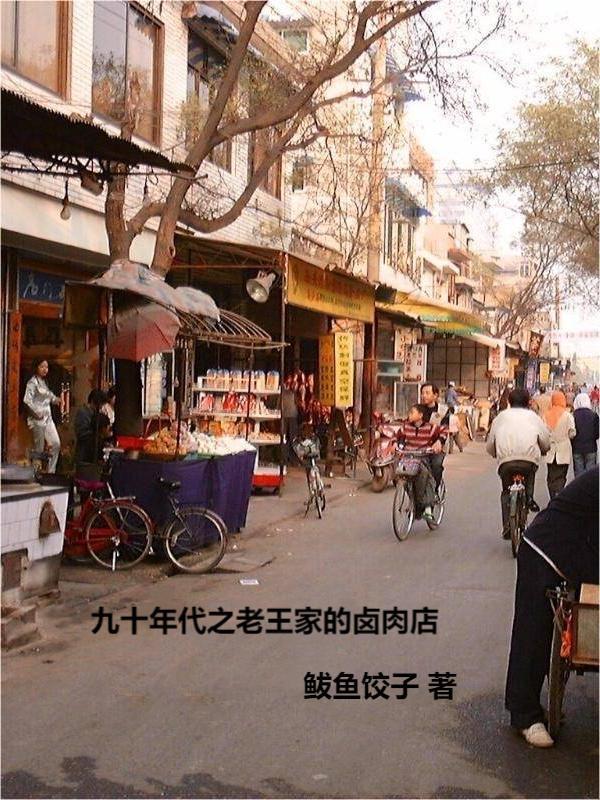大雨文学>快穿:被迫悖德边缘疯狂试探 > 第436章 龙傲天文里的小师妹41(第1页)
第436章 龙傲天文里的小师妹41(第1页)
他贪婪地呼吸着,整个身子都在剧烈抖。
直到这一刻,直到真真切切感受到怀中这具身体的柔软,温热和心跳。
那根紧绷了太久的弦,骤然崩断。
压抑了许久的恐惧痛苦绝望,还有那些连他自己都不敢奢望,卑微的期盼,如同决堤的洪水,轰然冲垮所有理智的堤坝。
他忽然放声大哭起来。
那不是成年男子克制的哽咽,而是像迷路孩童般嚎啕,破碎的哭声。
滚烫的泪水汹涌而出,瞬间浸湿了姜袅袅肩头的衣料。他哭得浑身抽搐,伤口因剧烈的呼吸起伏而撕裂得更深,却浑然不觉,只是死死抱着她。
一遍又一遍地,语无伦次地重复:“对不起……袅袅……对不起……”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别赶我走,求你了……袅袅……别不要我……”
声音嘶哑破碎,混着哽咽和抽泣,每个字都像从血肉里挖出来的一般,沾满了血淋淋的悔恨与恐慌。
他用尽手段将她绑在身边,以为恨比爱长久,以为占有即是拥有。
可直到此刻,直到他狼狈如丧家之犬地匍匐在地,直到她愿意蹲下来,用那双他曾伤害过的手擦去他的眼泪。
他才绝望地明白。
他从来要的都不是她的恨。
他要的,不过是她一瞬的垂怜。
百年光阴,于修仙者不过弹指一瞬,于凡人却是半生沧桑。
庭院里的那株绿梅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如今又是深秋时节。
姜袅袅裹着厚厚的银狐裘,斜倚在铺了软垫的躺椅上。
玄凌百年来以仙元温养,又以无数天材地宝细细调理,她的容貌依旧停留在二十出头的模样,肌肤莹润如初雪,眉眼娇艳如春花,连唇色都是天然的嫣红,眼波流转时,仍有少女般的灵动媚意。
可那具身体,内里却已衰败了。
她如今极易疲倦,稍受风寒便要咳嗽许久,指尖总是冰凉,再厚的裘衣也暖不透骨子里的寒意。
此刻她半阖着眼,望着院子里正弯腰修剪梅枝的男人。
他已彻底是凡人之躯。
百年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痕迹,却未曾折损那份与生俱来的英俊。
他身形依旧挺拔高大,肩宽腿长,穿着简单的靛青色深衣,腰间松松系着带子,衣襟微敞,隐约可见线条利落的锁骨与胸膛。因早年不曾在意容貌养护。
后来又怕自己老态太甚惹她嫌弃,偷偷求玄凌帮他缓了衰老之,如今瞧着约莫四十出头年纪。
岁月赠了他眼角细细的纹路,不显苍老,反添了几分沉稳风霜的韵味。
下颌线依旧清晰,鼻梁高挺,薄唇微抿时,仍有当年魔君不怒自威的轮廓。
只是那头墨,已掺了星星点点的银丝,在秋阳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倒为他平添了几分儒雅。
他察觉到她的目光,直起身,转头望来。
四目相对。
墨景然眼底瞬间漾开笑意,那笑意驱散了眉宇间所有的冷硬,温柔得不可思议。
他放下花剪,大步走来,衣摆带起几片落叶。
走近了,他单膝蹲跪在她躺椅旁,温热的大掌自然而然覆上她冰凉的手背,轻轻拢住。
“醒了?”他声音低醇,因年岁添了几分磁性的沙哑,“才睡了不到半个时辰,要不要再躺会儿?”
姜袅袅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他。
阳光透过稀疏的梅枝落在他脸上,照亮他眼角的细纹,照亮他鬓角的银,也照亮他看着她时,那藏也藏不住,滚烫而专注的情意。
百年了。
这个曾经偏执疯狂的男人,如今每日晨起为她梳,午间哄她用药,夜里握着她冰凉的手脚,一遍遍用体温去暖。记住了她所有饮食的喜好与忌讳,连她一个蹙眉,都能让他紧张半晌。
她抬起另一只手,指尖轻轻抚上他眼角。
墨景然呼吸一滞,任她触碰。
“有皱纹了。”她声音很轻,带着刚睡醒的软糯。
墨景然低笑,将脸往她掌心贴了贴:“嗯,老了。”语气里没有遗憾,反而有种奇异的满足,“这样才好,我们总算像一对寻常夫妻了。”
寻常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