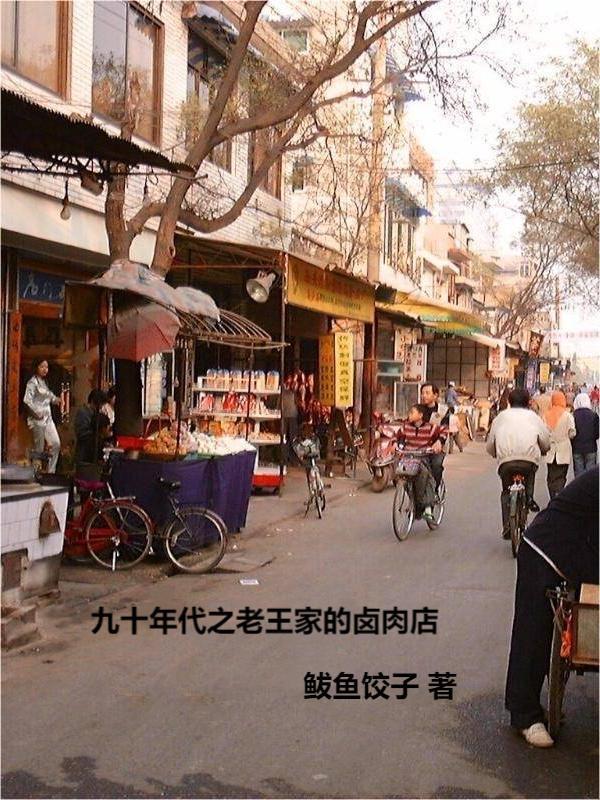大雨文学>和脱衣舞女郎妈妈一起穿越到异世界 > 第12章 妈妈跳脱衣舞诱惑黑狼王(第13页)
第12章 妈妈跳脱衣舞诱惑黑狼王(第13页)
转过身。
背对着他。
那背影更要命。
那背光滑的,白的,上面什么也没有,只有那文胸的带子横着,细细的两根,在那白皮肤上画着两道黑线。
那腰细得不像话。
那臀——
那臀就在他眼前。
就在他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
那两瓣臀肉在那火光里泛着光,圆圆的,鼓鼓的,中间勒着那条黑带子,那黑带子嵌在沟里,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
那印子随着她的动作一动一动的,一颤一颤的,像在说话,像在邀请。
她开始扭那臀。
对着他扭。
那扭不是刚才那种扭——那是更慢的,更用力的,更故意的。
她故意把那臀往后翘,翘得那沟更深了,翘得那黑带子勒得更紧了,翘得那两瓣肉都快碰着他了——
黑狼王的呼吸变得很粗。
粗得像牛喘。
他抬起手。
那只手粗糙的,黑的,满是老茧,指头上还有干了的血印子。
他想摸。
想摸那臀。
可他的手停在半空中。
没敢落下去。
因为她在跳。
在跳神女的舞。
在跳祈福的舞。
他的手就那么举着,像一只僵在那里的爪子。
她扭了一会儿,又转回来。
面对着他。
那脸上全是汗。
那汗在那火光里亮亮的,从额头淌下来,淌过眉骨,淌过眼睛,淌过脸颊,淌到嘴角那个破了的痂上——那痂被汗浸着,更红了,更像一滴血了。
她喘着气。
那胸随着喘气一起一伏的。
一起——那文胸被撑得更满了,那两团肉更鼓了,那左乳上的朱砂痣更高了。
一伏——那文胸松一点,那两团肉软一点,那朱砂痣低一点。
那起起伏伏的,像两座会动的山。
黑狼王的眼珠子跟着那一起一伏转。
转得都快掉出来。
她又抬起手。
那手白白的,细细的,沾着汗,在那火光里亮亮的。
她把那手伸到脖子后面。
摸到那文胸的带子。
然后她开始解。
那动作很慢。
慢得像那年在出租屋里她第一次脱给我看的时候——那种慢。
那带子松了。
那文胸从前面滑下来一点。
就一点。
露出那两团肉的上半截。
那上半截白得像雪,圆得像碗,上面还有细细的、被蕾丝压出来的印子。那印子一道一道的,在那白皮肤上画着看不见的花纹。
黑狼王的喉咙里又出一声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