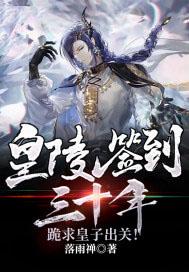大雨文学>李世民与渔家女曹婉儿的邂逅情缘 > 第181章 天牢夜决(第3页)
第181章 天牢夜决(第3页)
“哦?”李世民眉梢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语气依旧平淡,“去见许敬宗了?他…可还安分?”
“陛下明鉴。”曹贵妃的声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沉重与无奈,“许敬宗…已然崩溃,神智不清,口中尽是些大逆不道、攀咬他人的疯言疯语。臣妾念其曾为陛下效力多年,不忍其临终前仍如此癫狂失态,辱及朝廷颜面,故…去送了他一程,也让他…死得明白些。”
她的话语滴水不漏,既点明了许敬宗的状态已无任何利用或翻案价值,又巧妙地暗示了自己此行是为了维护皇家尊严,让罪臣体面(或者说,按照她的方式“体面”)地接受结局。
“死得明白?”李世民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榻的扶手,出沉闷的声响。
他目光锐利地看向曹婉儿,“爱妃让他明白了什么?”
曹贵妃微微抬头,迎上皇帝的目光。
那双凤眸清澈依旧,坦坦荡荡:
“臣妾只是将一些…他自以为无人知晓的陈年旧事,物归原主罢了。让他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所作所为,并非无人知晓,只是…时候未到。”
她没有具体提及玉佩和账目,但“陈年旧事”、“物归原主”几个字,已足够让李崇山明白其中分量。
这是在告诉皇帝,许敬宗的罪,证据确凿,根深蒂固,非一日之寒,也非空穴来风。她曹婉儿,早已洞悉一切。
李世民沉默了片刻。殿内只剩下龙涎香燃烧的细微噼啪声和他手指敲击扶手的笃笃声。
空气仿佛凝固了。高力士的头垂得更低,后背渗出冷汗。
他深知,此刻皇帝心中必然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对许敬宗背叛的震怒,对曹婉儿手段的忌惮,对承烨在边关孤军奋战的忧虑,以及对朝局即将迎来更大动荡的预判。
终于,李世民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波澜:“爱妃有心了。许敬宗…咎由自取,死不足惜。明日行刑,由三司监刑,昭告天下,以儆效尤。”
他做出了最终裁决,为许敬宗的命运盖棺定论。同时,这也意味着他认可了曹婉儿今夜的行动,认可了她提供的“明白”,并以此作为对许敬宗最后的盖棺定论。
他的目光转向案上那份未拆的加急文书:“承烨那边的消息,也快到了。”
曹婉儿目光微闪,顺着皇帝的视线看去,轻声道:
“殿下在北境苦战,力挽狂澜,生擒敌酋,想必军报之中,必有详实战果与…重要证供。许贼通敌,铁证如山,殿下此举,是为国锄奸,大快人心。”
她不着痕迹地为承烨表功,同时再次强调了“铁证”的存在,将许敬宗的罪责坐得更实。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李世民“嗯”了一声,不再说话,只是重新拿起那枚白玉镇纸,目光变得悠远。他仿佛透过这冰冷的玉石,看到了北境的风雪,看到了朔州城头的浴血,看到了天牢深处的绝望,也看到了这紫宸殿外,无数双在黑暗中窥伺、在风暴边缘等待时机的眼睛。
许敬宗倒了,但这绝不是结束。
拔起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带出的泥土下,必然还藏着更多的蛇虫鼠蚁。
朝堂的格局将被打破,权力的真空需要填补,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而他这位看似沉静如水的贵妃,以及那位远在边关、手段凌厉的亲王,无疑已在这场风暴中,牢牢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
曹贵妃静静地侍立着,眼观鼻,鼻观心。
她知道皇帝需要时间消化,需要权衡。她今夜的目的已经达到:
亲手为许敬宗送终,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掌控力与不可或缺,同时为承烨即将送达的“铁证”铺平道路,确保许敬宗再无一丝翻身的可能。
至于皇帝心中那丝可能的忌惮…曹婉儿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微光。
在这深宫之中,在这权力的旋涡中心,谁又能真正毫无保留地信任谁?
她所求的,不过是掌握主动,在这惊涛骇浪中,为自己,也为她想要守护的人,争得一方稳固的立足之地。
殿外的寒风,似乎更猛烈了些,拍打着厚重的窗棂,出呜咽般的声响,如同无数亡魂的低语,预示着长安城这个漫长的冬夜,以及随之而来的黎明,注定不会平静。
西市口的刑场,已在悄然布置;宣政殿的御案,即将迎来那份染着北境风霜与鲜血的、决定性的口供;而紫宸殿内的无声较量,仍在继续。
这座皇城之下,权力的暗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度涌动、碰撞,酝酿着下一场更猛烈的风暴。
喜欢李世民与渔家女曹婉儿的邂逅情缘请大家收藏:dududu李世民与渔家女曹婉儿的邂逅情缘小说网更新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