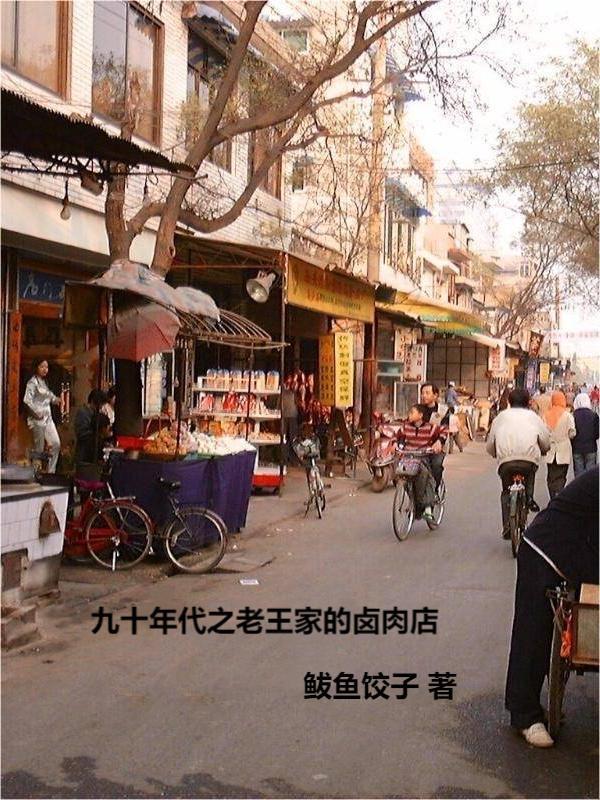大雨文学>南方的鹅北方的风 > 第233章 墓中角斗暗影低语(第1页)
第233章 墓中角斗暗影低语(第1页)
……
午夜零时四十五分|“坟墓”地下三层·第七区监牢
黑暗是这里的唯一统治者。
范智帆坐在冰冷的合金床板上,电子镣铐的幽蓝指示灯在绝对的黑暗中切割出时间。他没有睡——在这种地方,睡眠是奢侈品,也是致命弱点。
他的耳朵正在工作。
三百米外,水管深处传来有节奏的敲击,摩尔斯电码的碎片:“新来的……亚洲人……小心”。左前方监室,压抑的啜泣声像被掐住脖子的猫。右后方,肉体撞击墙壁的闷响,一下,两下,三下——某种自我惩罚的仪式。
走廊尽头,看守站的对话透过厚重的门缝挤进来:
“……号,什么来头?”
“档案上写着‘国际商人,涉嫌多项重罪’。但上头交代‘特殊处理’。”
“特殊处理?就那个身板?我看‘碎骨者’能把他当早餐吃了。”
“闭嘴。上个月那个华尔街来的律师,看着更文弱,结果在淋浴间用牙刷捅穿了两个人的喉咙。”
对话戛然而止。
范智帆缓缓睁眼。灰蓝色的瞳孔在黑暗中如两粒寒星。这间囚室他早已“阅读”完毕——三米乘二点五,特种钢一体成型,无窗,唯一的开口是门下十五厘米的送餐口。
(范智帆内心:年马库斯·莱恩设计的“沉默盒子”。专用于关押高智商罪犯或政治敏感人物。通风管道直径九点五厘米,内置红外激光栅。墙体夹层有压电陶瓷震动网,五百克以上的位移就会触警报。)
他重新闭目,调整呼吸。
五分钟后,一阵轻佻的口哨声由远及近。
脚步声停在门外。
“嘿!新来的!”沙哑的男声透过观察孔传来,带着布鲁克林街头特有的油滑腔调,“听说你把那个日本矮子干掉了?牛逼啊兄弟!”
范智帆没有回应。
“哟,还挺酷。”观察孔外,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睛凑近,“我叫艾伦·李·麦克斯——叫我艾伦就行。我在这鬼地方待了十二年,见过的硬茬比你吃过的汉堡还多。”
沉默。
“不过呢,”艾伦的声音忽然压低,带着街头混混传递情报时那种故弄玄虚的调调,“免费送你个消息。今晚……有人想弄死你。”
范智帆的睫毛几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
“别问是谁,问就是‘这儿的规矩’。”艾伦嗤笑一声,“规矩比法律好使。总之,你要是能活过今晚……咱们或许能交个朋友。对了——”
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异常平静,平静得像在陈述天气预报:
“别想着出去。我判了五百年。五百年。你懂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他们给我定的罪,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但他们需要我永远闭嘴。这里是美国,兄弟。有些判决,不是为了正义,是为了……清理。”
脚步声远去。
口哨声重新响起,调子是《友谊地久天长》,在死寂的走廊里扭曲成送葬的安魂曲。
范智帆缓缓坐直身体。
(范智帆内心:五百年刑期。象征性判决,意味着此人是“永久性危险品”。他知道什么?为什么需要被永久沉默?)
他看向腕上的电子镣铐。幽蓝的指示灯每隔十五秒闪烁一次,像垂死者的脉搏。
(范智帆内心:想让我死在今晚。手段无非三种——毒杀、意外、或“合法暴力”。如果是后者,地点大概率在……“放风区”或“工作坊”。)
他重新躺下,呼吸节奏改变——吸气如鲸吞,呼气如抽丝。心跳频率缓缓下降:o……o…最终稳定在每分钟次。
深度休眠状态。身体机能降至最低,意识悬浮如水面浮标。
等待。
凌晨二时十七分|“坟墓”中央天井区
脚步声响起。
不是一个人的。是三个人的——沉重、同步、机械。靴底敲击混凝土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层层回荡,像死神在敲钟。
整层监牢的“住户”们,在这一刻同时醒来了。
没有惊呼,没有骚动。只有无数双眼睛贴在观察孔上,瞳孔在黑暗中反射着应急灯的幽光,像墓穴里的萤火虫。
他们知道这是什么声音。
“清道夫”来了。